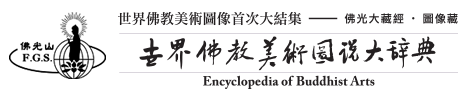內文搜尋 >
頁 碼:17/1_18
|
篆刻卷總論
篆刻總論.丹心印禪
游國慶 臺北故宮博物院 教育展資處 副研究員
以濡朱鈐印的篆刻藝術,善於在方寸之間展現無窮變化──
納須彌於芥子、見智慧以毫芒。
濡朱殷紅、似丹心之赤忱;守心貞定、若方寸之不亂。
以小識大、探賾知著;明心見性、禪趣相生。
此文人雅士之所以衷情於斯也,
故名之曰:「丹心印禪」。
一、印章源流
(一)殷商至西周──璽印的萌生期
殷商(約16世紀~11世紀 BCE)至西周(約11世紀~771 BCE)是璽印的萌生期。印章起源於西元前一千二百多年的商代晚期。臺北故宮博物院現藏有商璽兩方,其中一枚「亞禽示璽」的璽文作亞形框內有禽鳥文,學者隸釋作「亞禽」或「亞離」;同樣的亞
禽文,也屢屢見於商晚期至西周早期的銅器上,可知是當時重要的家族徽號。
亞禽示璽的印身扁薄,印面朱文凸起,亞形框略有殘損,印背有一鼻鈕,用以穿綬繫帶。既可鈐蓋於待燒的常用陶器上,以標示所有權;也可以抑按於陶範上,再翻鑄成銅器內底或足下的「族徽」,以成為祭祖禮器的一部分:用清楚標識著徽號的成組家族祭器,來陳設敬拜,榮顯先祖。這是中國璽印最早的使用狀況。
它擺脫了作為陶器外表上打印花紋的「印模」原型,與文明的禮制相結合,不僅體現了後世「印章」的鈐蓋、取信、標示權屬、可重複使用等功能定義,更有鈕孔用以穿綬佩戴,開啟了簡帛時代(夏商至東漢魏晉,約21世紀 BCE~420)印章佩掛以表身分(如:戰國晚期,約2 75~2 21 BCE,蘇秦佩六國相印)並封檢(抑壓封泥防奸偽)的古璽印風潮。
西周以宗法封建的血緣關係維繫政治的運作,天子與諸侯國之間的重大事件,往往鑄載以銅器銘文。除了部分商遺族還在銘末標誌族徽外,周人所作的銅器多不標族裔(因為都是姬姓的封國),反而在銘文結尾加上「子孫永寶」等祈福語,把對過往先人的祭祀追孝、對現世本人的企求長保尊貴,以及對未來子孫能永遠承繼榮耀的渴望心態,表露無遺。
傳世最著名的西周璽印,是曾著錄於《伏廬藏印》,而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一枚「鳳鳥紋璽」(王壯為先生嘗模刻多方,一方現貯臺北故宮,一方貯紐約張隆延先生處,印拓圖像則為臺北歷史博物館用為館徽),鳥首回顧、羽翅翩翩,與商晚期至西周中期在銅器和玉器上常見的鳳鳥紋樣可以參證。
(二)春秋戰國──璽印的勃發期
春秋(約770 ~476 BCE)戰國(約476~221 BCE)是璽印的勃發期。這個時期貴族陵替、諸國征戰、商業勃興、個人意識盛行,在政治、經濟及物質與精神發展的多重因素下,促成璽印的蓬勃發展。
貴族陵替、平民崛起,使以前藉宗族血緣作為政治權力的維繫紐帶失去功效,各國君諸侯與大夫的任官用人,都需要有可以清楚憑證的信物,於是授官「璽印」的鑄製與使用大興。
諸國征戰、兵書往返,使檄文書簡的用量大增,而信函的傳送過程中,往往用繩結與泥封加固,再蓋上印章封檢,以免中途被敵人窺視,致機密外洩。現存大量戰國迄魏晉(220~420)的封泥遺物,正相應著當時用印的普遍狀況。
商業勃興、設關抽稅,各國為求取自身利益,於各交通要道普設關稅稽徵,驗貨納稅後,便鈐蓋以通關印記,以燒熱的銅印烙蓋於木條上或馬身,作為繳稅證明。
個人意識盛行,作為代表個人的姓名字號印十分流行,另外,鑄有勵志箴言和祈福吉語的璽印也不在少數。這些印章用以佩戴或鈐印於封泥及織品上,代表個人的身分與思想情懷,一如諸子百家的興盛,是個人主義與古典藝文的高潮表徵。
(三)秦漢──璽印的鼎盛期
秦(221~207 BCE)漢(206 BCE~220)時期是璽印的鼎盛期。秦帝國與漢王朝是中國一統政權的先驅,政治的穩定與制度的確立,使印文所用的字體鎖定在「篆書」:商西周璽文用「大篆」、戰國用各域「古文」、秦用「小篆」而略見方折;篆體雖異,卻
都是當時通行的書寫常用字體。
至西漢(206 BCE~25),通行的書寫字體已逐漸轉變為「古隸」、「八分」隸書,然在印章上仍沿襲小篆結構,而愈加規整成「繆篆」──從此以後,「篆書」成了官私印刻鑄時的主要字體,無論同時代的書寫文字,不斷地由篆書演變成隸書(出現於西漢早中期,206~74 BCE),至草書(出現於西漢中晚期,140 BCE~8)、行書(出現於東漢前期,25~105)、楷書(出現於東漢後期,106~220。至此,中國漢字形體的「篆隸草行楷」各體都已完全產生,往後的書家,於「書體」不再開創,卻在「書風」的個人藝術上展現更多,遂形成璀璨的中國書法史,而官方通行字體皆為楷書),在印章的徵信和古典的基本追求下,「篆字」仍舊是治印者的最佳選擇。職此之故,刻製印章一道,往往也以「篆刻藝術」名之──用篆書刻印的一門藝術。
(四)魏晉南北朝至元代──璽印的轉變期
魏晉南北朝(220~589)至元代(1271~1368)是璽印的轉變期。魏晉南北朝時戰亂頻仍,治印一係承繼漢末頹風而日趨簡率,又隨美術雜體篆的興起,出現「懸針篆」等變體篆文印;一係由於書寫質材從簡帛轉變為紙張,用印也從鈐抑封泥改為濡朱之故,印面變大、印文線條由寬白文(陰刻)變細朱文(陽線),南齊(479~502)時的「永興郡印」是極佳的例證。
隋(581~618)唐(618 ~907)五代(907~960)是中國第二個統一強盛期,與秦漢時期並稱為「漢唐聲威」。二者相較,秦漢是漢字各種形體(篆隸草行楷)的創發與完成期、隋唐是漢字各種書體(篆隸草行楷)的風格創變與再生期;秦漢用簡牘書
寫,故印章用於封泥按捺、隋唐易以絹紙,故印式加大並濡朱泥鈐蓋。
秦漢時的官印與私印的形制大小和印文風格相近,隋唐以後則官私印分流,官印喜作「九疊篆」朱文寬邊大印(部分低階「朱記」用隸書),私印則或仿漢印、或作雜篆。
至宋(960~1279)、元的官印沿襲隋唐五代,私印出現了特殊的「押印」,圖書收藏、書畫鑑藏印記,以及文人齋館印等,與書畫家本身的姓名字號章,一起豐富了書畫圖書的鑑賞世界──這個由隋唐開啟的書畫「鈐朱」與文人署印的風尚,到元末蔚為大成。吾丘衍《學古編》的印學討論、王冕等人以花藥石刻印、《集古印譜》的出現,都在在透露出璽印篆刻的新時代即將來臨。
(五)明清──璽印篆刻的再生期
明(1368~16 4 4)清(1644~1911)是璽印篆刻的再生期。早期璽印材質主要為銅、玉,其鑄刻碾琢都需要專業的工匠來進行,因此,往往由文人、書手布好印稿後,再交給匠師完成。工匠多不具篆學素養,只能依樣畫葫蘆,其摹寫轉拓與刻製間,就不免有走形和線條乏篆趣等問題,而文人又難以動刀在堅韌的銅玉(摩氏硬度6~7)上修改,所以治印一事不易普及。
元末文人覓得花藥石(摩氏硬度2~3),石軟易受刀,於是開啟了文人自書自刻的風氣。沿及明清,參與刻印的文人愈來愈多,逐漸形成各種不同的流派,所謂「吳門派」、「新安派」、「歙派」、「浙派」、「皖派」等,風貌多變、各擅勝場,其藝術創發的精彩與多元,遠勝於同期的官印,是以學者習慣將此期的璽印重點放在這些文人書畫用印上,稱之為「篆刻流派印」──篆刻治印,從此與詩、書、畫三者,一同成為文人藝術創作的「四絕」。
(六)民國──璽印篆刻的集成期
民國是璽印篆刻的集成期。清末崛起的篆刻大家,流風扇及民初,如吳昌碩(吳派)、齊白石(齊派)、黃士陵(黟山派)、趙古泥(虞山派)等人,治印風格鮮明,從學者極夥,臺灣篆刻家吳平先生,猶是虞山的再傳弟子。
隨著流派師門的分衍,篆刻社團也於各處蠭起,如杭州的西泠印社、臺灣的印證小集(後改名「臺灣印社」)等。近現代印人取法古璽、漢印、鳥篆、元朱,以至於浙、皖、吳、齊各派,與古為新;不僅印內求印,更上取殷商甲骨、西周金文,下探戰國簡帛、貨
幣、陶文,乃至秦漢石刻、簡牘篆隸章草,匯而入印(所謂「印外求印」),使「篆刻」藝術,與漢字書法完美結合,且藉由運刀的巧妙變化,造成崩蝕鏽接等古老金石趣味(米芾稱「籀篆妙古老焉」),以刀作書而愈勝於書。這精緻刀筆又擴及於印石邊款,各體書風、造像圖紋,都可以在促而不狹的印側從容展現,簡直令人目不暇給。
二、文人與漢字、書印
(一)文人與印
作為文人遣懷絕詣的「詩、書、畫、印」四項,於吟詠寫刻間,自然流瀉對生活的感觸與生命的感動。當佛教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因其教義與中國固有的儒、道哲理相近,迅速進入知識分子的生活領域後,隨著時代的更迭,藝術形態的轉變,又逐漸微收於文人印家腕下的方寸之間。漢印多僅一寸(2.3公分)平方大小,故藉以為印面範圍的代稱──在約莫「方寸」的狹小空間,可以寄託印人的無限心量,以及廣闊無羈的藝術表現;雖小實大、似微實巨,故曰:「納須彌於芥子、見智慧以毫芒。」
(二)漢字與書法
文字在發展之初便與書法結下不解之緣。甲骨文多以刀刻(多未寫直接刻,部分先寫後刻)、金文多由陶範書寫後翻鑄,但其平日記事恐怕還是以毛筆寫於簡牘帛書上居多,可惜竹木縑絲易朽,近年出土只有戰國簡帛,商與西周的已不得見。
董作賓研究殷商甲骨文,提出書體斷代,將盤庚到帝辛共二百七十三年的殷墟階段分為五期,每期各有不同的書風(一期雄偉、二期謹飭、三期頹靡、四期勁峭、五期嚴整)與特殊字形寫法。
西周文字以金文為大宗,從武王(1134~1116 BCE在位)到幽王(781~771 BCE在位)二百七十五年,其間文字也可依其書風分為三期:早期承襲晚商,書風多雄肆、線條較清勁,如「卯必甗」銘。中期漸趨整飭,線條較婉秀、書風偏規整,如「同師簋」。晚期金文的結構更形嚴整、布局疏朗、筆道均勻,如「兌簋」。但也有較奔縱放逸的傑作,如「散盤」。
春秋戰國以後,各文字異形增多,加以記載文字的質材多樣(銅禮器、兵器、貨幣、璽印、陶文、石刻、木器、簡牘、帛書、漆器等),更經書寫、刻劃(單刀或雙刀)、翻鑄、捺印等文字製成工序,使漢字呈現多采多姿的特殊風華。史書上說「秦書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新莽六書」(古文、奇字、篆書、鳥蟲書、繆篆、左書),大致反映了古文字階段的文字多樣性與其美術應用的多元化。
兩漢以後,隸、草、行、楷,踵事增華,歷代書家輩出,篆書也不斷翻寫出新,競秀爭妍。無論就書體的多元多樣或書風的奇正變化,縱貫三千多年的漢字發展,放諸寰宇,必然是獨占鰲頭且風騷絕代的。
擁有篆、隸、草、行、楷各體各形的漢字,在圓錐形毛筆的驅遣下,幻化成中國書法史上的琳瑯墨寶,用空間、布局、行氣、結體、線條、筆力、墨韻,留給後人一個最美的玩賞視界。
而印章,也陪伴著書體的演變,尤其是篆書的時尚變遷,有不同的風格展現。
(三)印與漢字
文人以毛筆為日常的書寫工具,其內心所思、筆下所書,自然呈顯其生命的主體傾向,而「漢字」即其資以表現的最基本元素,「治印」篆稿布局尤其離不開「漢字」。中國字有很多種,滿文、藏文、契丹字和漢字等都是「中國文字」的一支。「中國」這名詞至遲在西周早期已出現,周成王(1115~1079 BCE在位)時的「何尊」上,即有「宅茲中或(國)」的銘文,各種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字的人群,在不同的時空加入「中國」的範疇,然而真正在華夏長久通行的文字,只有「漢字」。
漢字約起源於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代(約21世紀~約16世紀 BCE),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商代便逐漸發展為成熟的文字體系。人們常說的「甲骨文」就是商晚期文字的主要資料。商代文字以甲骨文為大宗,還有少數的金文(銅器上的鑄銘)、陶片刻文和玉石上的朱書、墨書等。有些金文的時代比甲骨文還早,因為比較零星,常被人忽略。由於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既豐富、其文字結構又已出現較完整系統(符合傳統文字學家的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各造字原則),所以一向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
甲骨文所代表的商代文字,不是世界最早的成熟文字,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比它早上數百千年,但楔形文字、埃及古文字後來相繼斷根,在當地改用拼音字母記錄語言,唯獨漢字則綿延三千多年,直到今天還生生不息地使用著。它由商代經西周,歷春秋戰國,到秦始皇(246~210 BCE在位)統一天下,一直以同一構形體系的籀文(大篆)、古文、小篆記錄各地語言;又由於結構的省變、偏旁的調整和筆法的改變等因素,在漢代發展出隸書與草書,東漢(25~220)晚期,更去掉隸書的橫勢波撇,逐步形成我們熟悉的行書和楷書。
同樣是記錄語言,在中國竟然有篆、隸、草、行、楷各種書體,因為毛筆書寫的多樣性,各書體之中,又有種種不同書風,尤其是在東漢以後各書體俱興、書寫工具與材料普及(紙的發明)之下,「書法」遂漸漸成為貴族間極端重視的個人藝術品味表現項目了,東晉(317~420)王羲之的絕妙尺牘名跡於焉產生。
「篆刻」的「印」,包含了印面與印身:印面用篆書為印文主體;印身邊款則以真草隸篆諸書作為變化的元素──亦即以漢字體系裡的各種字形為治印的根本取材。雖然,在中國印史上,還偶爾出現契丹文、蒙文、滿文、藏文等少數民族印,但真正的中國「篆刻」,仍是以「漢字」入印為主流的,這與定義「中國書法」為「以毛筆書寫漢字的一種線條藝術」,以標舉「漢字」命題,是同樣的道理。
三、佛教與篆刻
(一)印人與佛法
「篆刻」既作為文人遣懷絕詣的「詩、書、畫、印」四項之一,則以文字、文學、文化滋潤身靈的印人,其對生活的感觸與生命的感動,必然於吟詠寫刻間,自然流瀉在刀下、石上。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漸漸與儒家、道家的哲思,同為中國文人的重要精神依託。即便不是茹素持齋、每日誦經拜佛,多數書畫家、篆刻家都有方外僧友、或有皈依釋師,如北宋(960~1127)的蘇東坡、黃山谷;元代的趙孟頫等人,諸書家與法師間的尺牘、翰墨、題辭、贈偈,乃至書家日常遣懷所流瀉的禪機慧語和前賢語錄,都充滿著佛智與法喜。在本辭典的「書法」部分有許多珍貴例證,我們在書法總論〈翰墨平生作佛事〉中曾經提及:
類此「交誼」書作,在本辭典中尚多,如宋蘇東坡的《次辯才韻詩帖》、釋道潛的《與淑通教授尺牘》、沈遼的《想望顏采帖》、大慧宗杲的《與無相居士尺牘》、元管道昇的《致中峰和尚尺牘》、馮子振的《贈無隱元晦詩》等,在書信、贈答、題辭、詩文,乃至圖贊跋記中,可以清晰呈顯當時高僧與高僧、高僧與弟子、文人與法師、帝后與禪師之間的各種交誼和互動──屬於人情與信仰生命最深刻誠摯的交往應答,在不同的墨跡筆觸裡,重新展現歷史。一個虔誠的宗教徒,不僅僅是誦佛修行、抄經回向,追尋宗教世界的「至善」;也有深入師友的互動,流露人性友情的「至真」;而提筆作字,抒發心靈之際,講究結字行款的妍麗樸茂、錯落變化,又何嘗不是一種藝術「至美」的求索呢?
同樣地,印人身處如此妙諦佛氛之中,自然會擷取其教義經典的精華,化為紀感、抒懷或勵志的印面布局,以一刀、一劃的細緻刻鏤,內蘊出佛教的豐富智慧;用致廣大而極精微的方式,結晶於印家腕下的方寸之間。本辭典所收的一百餘方篆刻名品,就是
在此前提下彙集而成的。
(二)佛經印文
所收各印,最多是佛經經句,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潘西鳳刻)、「遠離顛倒夢想」(張樾丞刻),語出《心經》;「我得無諍三昧」(陳豫鍾、朱復戡刻)、「不住於相」(李大木刻),為《金剛經》句;「金粟如來」(張在辛、中村蘭台刻)、「淨土」(蔣仁刻)擷句於《維摩經》;「勇猛精進」(陳師曾刻)、「真實不虛」(陳半丁刻),取源《大般若經》;「不二法門」(楊汝諧刻)、「深入無邊」(簡琴齋刻)、
「一切惟心造」(張大千刻),見諸《華嚴經》,凡此種種,大概皆是文人印家平日習佛誦經有感而作,鈐於書畫圖籍,藉表心思所寄,或資以自勉修持、以上企及之。
(三)僧人治印
較特殊的幾方僧人治印:萬壽祺(入清為僧)刻「春山書畫綠楊船」、釋明中刻「且擁圖書臥白雲」、釋佛基刻「樂莫大於無憂」、釋篆玉刻「我靜如鏡」、悟心元明刻「悟心別號九華」、釋達受刻「六舟在新安所得書畫印」、釋見初刻「小素」。前二印「春山」、「白雲」,無非禪機;第三至五印,「隨喜」、「無憂」、「如鏡」是心性的大修持;末三印為僧人自用書畫鈐記之印,可知出家為僧並不絕斷於書畫印藝,殆因藝術中之至美、至善、至真的全然展現,實與宗教修持對生命價值的了悟並無二致,這從弘一法師出家後的書印雙絕,可得明證。
(四)刻印若刻經
佛經是佛教傳遞弘揚的重要文字資料。隨著紙張的盛行,抄錄佛經以供誦讀、學習,以普及四方,漸漸形成風氣。西漢末年哀帝元壽元年(2 BCE),大月氏派伊存出使中國,伊存以口授佛經予博士生景盧,景盧筆錄之,史稱《浮屠經》,為最早之漢文佛典,惜傳抄至西晉(265~316)以後散佚。
早期的抄經,多由經生等專業抄手為之,唐時始見書家偶有致力於寫經、以供刻碑者,如柳公權書《金剛經》。明清印人將抄經和刻經融為一爐的最佳傑作,則是以數十方印石分鐫《心經》經句的套印組,據傳鄧石如等名家均嘗措手於斯(鄧石如另有於嘉慶八年(18 03)篆書的《心經》作品,參見本辭典之《書法卷》),本辭典收錄黃士陵刻《心經》五十二套印之一,殆礙於篇幅,無法全數納收,但嘗鼎一臠,可以知味矣。
(五)印與造像題記
北朝(386~581)石窟中有許多佛教造像及題記,其造像記的刻銘書法,氣勢閎偉、刀斧森然,早為書史楷法魏碑體的重要資料。印人取之入印,如趙之謙刻「●(汲-及+食)經養年」印,於印身一側作佛陀造像,另三面擬北魏《始平公造像》的陽文題刻與書風,畫以陽線界格而書刻之,以成四面邊款;全印渾然一體,極精雅生動、耐人玩味。
趙之謙開啟了佛教造像及北碑題銘書風入印身,從而擴大篆刻的表現形式後,仿傚此法刻治邊款的印藝,迅速蔚為風潮,如易大厂的「蔭堂經藏」、趙石的「芥彌精舍」、朱復戡的「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都是在四邊印側刻以生動的造像,以及鮮活多姿的各體題記,畫法、書風各異,別開生面。
至於鄧爾雅所刻的「一切眾生皆得佛右」,則將造像與題記均刻於印面,用以直接鈐蓋朱泥,不似前者須經耐心墨拓,可以廣為流傳,遂又新啟一種刻製造像的不同風氣,如豐子愷、來楚生、王壯為等人,都是箇中翹楚,留下許多極精彩的肖形佛像印。
四、結語
揚雄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意似貶抑篆刻一道,實則不然。璽印篆刻,涉及印學史、篆書史、篆刻史、書法史,其理論與鑑賞的培養,絕不減於書道的學習,而治印對刀法的講究:中鋒、側鋒、衝刀、切刀的使運差異,又非熟諳此道者所能體會。故欲治一印,初須有篆法、字法以布稿,次須有筆法、刀法以刻成。印面既就,於邊款更須有辭章文采以撰稿、有能驅遣真、草、隸、篆各體書之手腕,加以造像、肖形等錯綜變化,始能完成一方豐富而細緻耐玩的不朽名印。「雕蟲篆刻」,豈是能草率輕忽者?是以王壯為先生取「壯為」為號──壯夫而為之,反用揚雄之語,更見此道之不易也。
印章的邊款,除簡單的名款外,抑或有單刀長款,以敘記治印緣由,其一字一句之間,俱見印人涵養與人際關係,如尺牘翰札之往返互動,恍然對面而語,讀者只要細讀各印旁款(尤以丁敬所刻「西湖禪和」、「明中大恆」二印的長款),玩味各印人治印刻石之由,那份生命交流的感動,自然會洋溢胸前。
一種存在於崇高宗教情懷下,人與人、人與事之間的真實再現,令人不禁從那一刀一筆一劃間,追想當時的敬穆景況;沿著朱泥鴻爪遊走,想見歷代印人、高僧以刀筆敬謹地驅遣漢字,化為極具生命感動的方寸印痕,因應著每一時空的生活體驗,成就出一方方真情流露的篆刻藝術,這正是佛教印藝最精萃、最動人之處。
|
相關詞條:吳昌碩, 齊白石, 黃士陵, 米芾, 蘇東坡, 釋道潛, 想望顏采帖 沈遼, 次辯才韻詩帖 蘇軾, 與淑通教授尺牘 釋道潛, 想望顏采帖 沈遼, 大慧宗杲, 與無相居士尺牘 大慧宗杲, 管道昇, 致中峰和尚尺牘 管道昇, 馮子振, 贈無隱元晦詩 馮子振,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潘西鳳, 潘西鳳, 遠離顛倒夢想 張樾丞, 張樾丞, 陳豫鍾, 我得無諍三昧 陳豫鍾, 朱復戡, 李大木, 不住於相 李大木, 張在辛, 金粟如來是後身 張在辛, 中村蘭台, 蔣仁, 淨土 蔣仁, 陳師曾, 勇猛精進 陳師曾, 陳半丁, 真實不虛 陳半丁, 楊汝諧, 不二法門 楊汝諧, 簡琴齋, 深入無邊 簡琴齋, 張大千, 一切惟心造 張大千, 萬壽祺, 釋明中, 且擁圖書臥白雲 釋明中, 釋佛基, 樂莫大於無憂 釋佛基, 釋篆玉, 我靜如鏡 釋篆玉, 悟心別號九華 悟心元明, 釋達受, 六舟在新安所得書畫印 釋達受, 小素 釋見初, 釋弘一, 柳公權, 鄧石如, 心經 鄧石如, 心經 黃士陵, 易大厂, 蔭堂經藏 易大厂, 趙石, 芥彌精舍 趙石, 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 朱復戡, 鄧爾雅, 一切眾生皆得佛右 鄧爾雅, 豐子愷, 來楚生, 王壯為, 丁敬, 西湖禪和 丁敬, 明中大恆 丁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