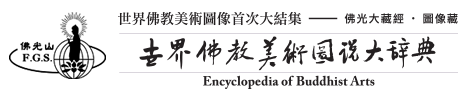內文搜尋 >
頁 碼:13/1_26
|
雕塑卷總論
總論.佛教雕塑藝術概論
林保堯│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專任教授
陳慶英│北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宗教研究所教授
嚴智宏│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緒論
佛教雕塑藝術源自印度,然而所謂的印度,並非今日印度的疆域,而是包含印度西北側的巴基斯坦、尼泊爾北方、不丹,以及東側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在內的古印度。自古印度開始興起的佛教,隨後向南北兩地傳播,即所謂的南傳佛教、北傳佛教。佛教的雕塑及藝術,也隨南傳、北傳佛教而傳布了整個亞洲地區,堪稱是亞洲信仰面積最大的宗教,同時也造就了亞洲最大量,最精質的宗教藝術與文化遺產。
從南傳佛教傳播路線觀之,包括今天的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的南亞以及緬甸、泰國、柬埔寨、寮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等的東南亞;北傳佛教傳播路線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地區,喀什米爾、西藏、尼泊爾、不丹、錫金等的藏印地區,以及越過帕米爾高原的中國地區,還有韓國和日本的東北亞,皆可見及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具各區域性的佛教雕塑藝術。今,擬大略述之。
一、印度
印度、中國、埃及、美索不達米亞,號稱古文明四國,然而對於印度的古文明,世人實在不甚了然,直至一九二二年前後,英國考古學家馬歇爾(John Marshall)主持印度考古局時,在印度河流域發掘出兩座古代城址,一是今巴基斯坦境內旁遮普(Punjab)印度河支流拉維河左岸的哈拉帕(Harappa),另一在信德(Sindh)印度河右岸的摩赫鳩達羅(Mohenjo Daro),始為世人所知。一九四六年後,英國考古學家等相繼發掘調查,發現不少印度河的類型古城址,統稱為印度河文明,亦稱哈拉帕文化,其分布面積南北約1,100公里,東西約1,550公里,遠超過埃及與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地區。其年代依英國考古學家研究,為西元前二千五百年至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換言之,印度文明的歷史可上溯到西元前三千年前,位居世界古文明行列。
約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印度河文明突然消失,其中一說,是約於西元前一千五百年至前八百年前,高加索雅利安人(Aryans)入侵,建立吠陀文化(恆河文化)。約西元前九世紀,雅利安人的吠陀教演變為婆羅門教,即印度教的前身。約西元前六世紀,北印度雅利安人的拓展逐漸形成一系列王國,相傳有十六列國,其中以恆河流域大國摩揭陀勢力最強。由於出身剎帝利種姓的王族,掌握國家政治權力,相對地在宗教思想上出現了剎帝利反婆羅門特權的思潮。在此因素下,耆那教與佛教相繼興起,正可說明當時宗教思潮的開展。
佛教教主釋迦牟尼佛的修行與教法,與婆羅門教、耆那教相互鼎立,成為印度早期重要的三大宗教之一,衍生的佛教藝術,為古代印度王朝中極重要的人類藝術文明標誌。
(一)早期佛雕
所謂的「早期」,即指西元前。早期人類的文明藝術,因種種歷史因素而消失,甚而被破壞殆盡,致使後人無從得知,古印度佛教雕塑藝術,同樣令人遺憾不已。佛陀入滅後兩百餘年間的佛教雕塑作品,雖然後有英國東印度公司於殖民期間考古挖掘調查,然文物卻都蕩然無存。目前所知遺存最早的佛教遺蹟就是孔雀王朝阿育王(約269~232 BCE在位)所立的石柱,其仍完整聳立如初的有勞里亞南丹葛爾(Lauriya Nandangarh)石柱及巴克拉(Bakhira)石柱。前者有銘文,後者則無。前者位於秣菟羅(Mathura)北4.83公里,勞里亞南丹葛爾故城遺址,南北二面分刻誥文,柱身研磨打滑,極富光澤,長有約10公尺,柱腳約90公分,柱頂約57公分。柱頭為鐘形,其上有圓板,圓板上有蹲踞的開口獅子,整體保存完整,僅獅口稍受損。圓板側緣列有頭低下的鵝鳥裝飾,極為典雅。鐘形以上到獅子頂,高約有208公分。另佛陀多次遊化說法的吠舍釐,亦有完整的阿育王柱。
阿育王柱的價值在其柱頭的雕刻藝術與柱身的誥文。就柱頭雕刻言,以阿育王遷都於鹿野苑的四獅子柱頭最為名滿天下。四獅頭頂有大石輪,象徵佛陀於鹿野苑初次說法。四獅子雕刻極為優美,從獅頭、獅身、獅爪,非常寫實逼真,尤其在獅身的毛髮中尚可見略帶裝飾的形式美,充分體現希臘藝術雕刻語彙,生動活潑。
人物上,在阿育王的首都華氏城(今印度巴特那,Patna)巴特那博物館內收藏的西元前二世紀藥叉女,堪稱古印度之代表作。此作不僅有堅實成熟的石雕表現技法,最重要的是人體立體圓雕的思惟語彙,將女性健美的體態逼真地顯現,完全不亞於當今人體寫實藝術。藥叉女本為古印度祈求多子多孫的地母神或母親神、婚姻神,故其女體特別突顯生命的豐滿堅實雙乳及肚臍下生育過的妊娠紋,刻劃代表地母神智慧的大白毫亦更為添美,實為古印度人體雕刻藝術之最。
孔雀王朝(約321~185 BCE)衰亡後,印度再度分裂,然佛教仍盛,此時北方以巽伽王朝(約187~75 BCE),南方以薩塔瓦哈納王朝(Satavahana,約200 BCE~250)為主,各留下足以驕傲的雕刻遺物。前者有巴爾胡特大塔、桑奇大塔,後者則有阿瑪拉瓦提大塔,其特徵在於不以人的形象表現佛陀,而代以菩提樹、佛塔、法輪、佛足等象徵物,即所謂的「無像時代」。遺留的作品大部分構圖較為簡單,人體比例不理想,姿態僵硬,然作風卻又十分樸拙。
另在人物的雕刻藝術,桑奇一號塔東門北柱第三橫梁下的藥叉女立像,可謂是完全成熟的立體人物雕刻技法。不僅體態多變,人體的三屈式掌握得惟妙惟肖,深具寫實手法的表現。桑奇大塔整體雕刻藝術已是重大突破,成為其後佛像雕刻藝術的先河。
(二)貴霜王朝
西元一世紀初,居於西北印度月氏族五部翕侯之一的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約30〜80在位)統一月氏各部落,在喀布爾河(Kabul)流域建立了貴霜王朝(約1~3世紀),至第三代君主迦膩色迦王(約129〜160在位)時,國力鼎盛,疆域達至蘇俄南部鹹海一帶,今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北部皆在版圖內,還曾一度入侵到東印度恆河流域摩揭陀國,遠到貝拿勒斯(Baranas,今瓦拉那西Varanasi),將貴霜統治中心從中亞移至犍陀羅地區,定都布路沙布羅(Purushapura,今白夏瓦Peshawar)。迦膩色迦王是印度史上著名的護法明君,曾在喀什米爾舉辦第四次經典集結,對佛教的流布具有極大貢獻。
貴霜王朝的佛教美術發展,開始有佛像和菩薩像出現。當時的佛教造像中心有犍陀羅及秣菟羅,雖二地文化背景相異,風格不同,卻是往後各地佛教雕刻藝術依附的母胎體。
1.犍陀羅
犍陀羅造像,正如法國美術史大儒福榭(Alfred Foucher)所言「以希臘人為父,以印度人為母」的歐亞混血兒。早在貴霜王朝以前的大夏人(Bactria,巴克特里亞),在西元前一百九十年征服了犍陀羅,建立了一個與大夏不同的印度-希臘王朝(Indo-Greek),且在呾叉始羅(今塔克西拉古城,Taxila)建立都城。在長達一世紀多的統治中,帶來了大夏人喜愛的希臘文化。西元前八十五年,中亞遊牧民族賽族亦入侵此處,控制了旁遮普。再者,西元前二十五年伊朗北方的安息人又從阿富汗中部入侵。賽族、安息雖信奉拜火教,然入侵之後正如大夏人一樣,亦受到佛教感化,創造了結合希臘及波斯的藝術風格。而在其後的貴霜王朝財力雄厚,與羅馬帝國貿易往來頻繁,漸而促使此地佛教雕刻造像帶有濃厚的西方色彩。
(1)起源論爭
一八四九年英國於印度設考古局與孟加拉工兵隊,在西北領屬地,即古代旁遮普附近,挖掘出很多不為世人所知的佛像,一時成為歐洲古董市場的稀品,同時亦開展出各國學者對所謂的「犍陀羅佛」起源處的百年論爭。當著力此課題,卻又出現比一八四九年出土還早,中印度一八三六年即有佛像出現紀錄的「秣菟羅佛」,也捲入這一場論爭洪波裡。百餘年來的論爭與努力焦點,就在於佛像起源究竟是犍陀羅?還是秣菟羅?而犍陀羅自身是希臘說?還是羅馬說?這四道課題。
(2)希臘說
希臘起源說,為福榭於一九一三年首先揭櫫,後其大著《犍陀羅的希臘式佛教美術》第二冊中給予了詳細的論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述的東西文明交流下歐亞混血兒說,然此說今已不成立,但其精深廣博的佛教圖像研究,至今仍不失其價值。英國考古學家馬歇爾自一九一三年起,長達二十二年在犍陀羅的呾叉始羅古城展開詳盡的佛像考古。一九五一年出版三冊《呾叉始羅》考古報告,一九六○年出版《犍陀羅佛像》,其結論雖然也同於福榭的希臘說,然論點因取自呾叉始羅,故見解異於前者。
馬歇爾的希臘說,今天雖不成立,然往後所謂的羅馬說,卻是建立在馬歇爾的論點上,其起源的探討中有一關鍵點,就是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的年代,馬歇爾採一二八年的說法,此時應即是西方的羅馬時代(27 BCE~476),但是馬歇爾卻未對犍陀羅的起源取名為「羅馬式的佛教美術說」等見解有進一步的說明。然而,他卻對西爾卡普(Sirkap)的遺跡發掘,明確地斷定:「犍陀羅佛像創始與起源,是無法追溯至貴霜王朝以前的。」如此重要且有依據的見解,便是後來學者走向羅馬文化影響的「羅馬起源說」催生劑。
(3)羅馬說
將犍陀羅美術中的西方古典因素,視為羅馬帝國文化影響的概念,其實是始自一八七六年的費格遜(James Fergusson)倡說的「印度-羅馬式」或「印度-拜占庭式」一詞。接著,史密斯(Vincent Arthur Smith)於一八八九年首度使用「羅馬式佛教美術」這個美術史專用術語。前述的福榭、馬歇爾希臘說,在一九四○年之後,因諸多英、美學者們更進一步的研究,使前述費格遜及史密斯的羅馬說,受到了新的評價。英、美學者們所把握的方法,是將羅馬美術與犍陀羅美術,直接從圖像、構圖、風格等各方面作比較,且將各類的類似性,逐一檢討。雖英、美學者們的研究都沒有列出有體系性的論述,又未必能超越福榭,但是所作的具體性與意義性,卻有極大的啟示。如迦膩色迦王之前,沒有任何一點證據顯示有過犍陀羅佛的出現,進而以犍陀羅和呾叉始羅出土的各類造像與羅馬帝政時期作品比較,從二者式樣風格上的類似之處,判定犍陀羅佛像非源自安息王朝(247 BCE~224)的希臘文化影響,而是貴霜王朝與羅馬的海上貿易交流結果。
又,從犍陀羅美術與羅馬美術比對,二者圖像式樣與構圖都相似,由此看出二者密切關係,例如早期犍陀羅佛與寬鬆外袍的羅馬皇帝奧古斯丁像(Aurelius Augustinus)幾乎是同一模子製作的;犍陀羅出土極多佛傳圖,異於中印度,然從其有理論性且形成一貫連環性製作來看,發現連環故事圖中,讚美神格化天人大導師的表現,只有在羅馬皇帝的崇拜美術上,才能找出相互援用又適合的答案。
另外,從主題意識與造型式樣論證「羅馬式佛教美術說」其功極大,如犍陀羅佛像的服飾造型,看不到希臘美術上將衣服明顯地表現體軀輪廓的特徵,而是衣服與軀體脫離,且具有量感,衣襞有如垂掛的窗簾或布幕,其深雕又平行的手法,接近一至三世紀初期的羅馬帝政時期美術,故犍陀羅最古佛像應是在一世紀末;再者,佛像衣襞作扭狀表現,像有次序的網繩狀布滿身體,除受到中印度秣菟羅美術影響外,同時也與帕勒米亞(Palmyra)、哈特拉(Hatra)的雕像衣襞有極度近似之處,故此類作品年代應為三至四世紀,即貴霜王朝與羅馬互相交流而誕生的。
羅馬起源說的論點,正如上述,在比較論的方法上皆有弱點,因欠缺有決定性的證據。馬歇爾建立在有根據性、確實性呾叉始羅發掘的考古證物上,反而受人重視,然重要的編年問題,在後來學者的努力下,作出明確又具說服力的成就。
總之,犍陀羅的佛像造型,源於印度佛教的靈感,主要汲取希臘化藝術形式,特別是借鑒貴霜王朝同時代的羅馬帝國藝術;犍陀羅佛像等於希臘化藝術的寫實人體,加上印度佛教的象徵標誌。故整體觀之,由希臘的太陽神阿波羅或希臘、羅馬哲人的頭部,加上披著羅馬寬長袍托格(toga),與某些表示佛陀的殊勝相貌特徵(即所謂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混合而成的這種希臘化佛像,即「阿波羅式佛像」,或「穿托格佛像」,同時表現出佛陀兼具凡人的形體與超凡的內涵。
菩薩像雖受到希臘藝術影響,然更富於印度色彩,帶有印歐混血兒的特徵,尤其高大的身形配上華麗的飾物,顯現貴霜王朝風度翩翩的印度王子形象。如法國巴黎吉美國立亞洲藝術博物館藏的菩薩立像,除帶印歐混血特徵外,俊美清秀,五官端正,全身戴精美配飾等,顯示出古代印度人的華麗氣派。
2.秣菟羅
秣菟羅位於印度德里南方,雅姆納河(Yamuna)西岸,距德里140公里的重要商業城市,交通便捷,可通往西海岸,又為貴霜王朝的東都。其雕刻藝術異於犍陀羅,極富印度色彩,具有強烈的本土風格,及極大的影響力,更使鄰近地區的造像與之接近,故謂秣菟羅風格。在材質上,採用當地西克里(Sikri)帶有米黃色或乳白色斑點的紅砂岩,成為秣菟羅雕像的重要標誌。
秣菟羅自古就是宗教聖地,且人才輩出。相傳佛滅後一百年時的七百結集大會,主宰其事者即是秣菟羅人;阿育王時代國王的重要佛教指導者優波笈多亦出身此地,再者,此地出土的貨幣和碑銘,可見到西元前二世紀至一世紀巽伽王朝統治此地的二、三位地方藩王之名,從遺品中亦說明當時此地佛教雕刻的史實。
一世紀末起,西北的貴霜族及塞族相繼來到,尤其貴霜族以此地作為印度的據守點,使秣菟羅的重要性大增,是時佛教、耆那教也於此地大盛。北方塞族此時亦侵入此地,例如著名的秣菟羅獅子柱頭,有佉盧文(Kharosthi)奉獻銘、詳記佛教寺塔的營造,以及當時統治者名字,就是庫沙吐拉帕斯王朝(Kshatrapas,約35~405)的最早遺品。接著貴霜王朝的迦膩色迦王時代,此地成為該帝國政經、軍事最重要據點。從當地秣菟羅博物館的收藏品,即可得知。
(1)貴霜王朝
秣菟羅雕刻早期遺物極少,從陶磚水神像的考古出土品看,近似大地母神的造型,大致是孔雀王朝或更早期之物,其後的巽伽王朝確實有了佛塔的存在,如欄楯浮雕等,和巴爾胡特佛塔比較,可知中印度的古代雕刻風格趨向簡單而樸素。貴霜王朝,可分三期:初興期(庫沙吐拉帕斯王朝),不過卻被後來的第一貴霜王朝勢力所包圍的時代;大盛期(貴霜王朝),其間秣菟羅美術大約興盛長達一世紀;衰退期(後期貴霜王朝時代),即第二王朝滅亡,到笈多王朝(約320~550)興起之間。
初興期,作品不多,卻留下極具創造性的作品。此時期秣菟羅美術造型相當活潑,燃起初興期起始的創作,引導出後來貴霜王朝蓬勃的美術活動,也就是最重要的秣菟羅佛像。
大盛期,即迦膩色迦王登基後的二世紀中葉,佛像與耆那教造像突增,產生了秣菟羅佛像與犍陀羅佛像先後的問題,當中就有倡議秣菟羅為佛像起源的論據,即前文所述佛像起源的世紀論爭。
衰退期,第二貴霜王朝就造型美術言極為重要,雕像內容除佛教、耆那教外,還有與當地民間信仰有關的,及印度教神像等皆一起出現。一般欄楯皆以裸體妖豔的藥叉女像最具特色,遑論國王、貴族的肖像,亦雕作不少。
秣菟羅的雕像從早期出土的各類藥叉女像觀之,裸體、妖豔,追求豐滿又肉感的女性表現為其傳統特色,但作品造型中帶有硬勢,甚而僵直的味道,從秣菟羅博物館藏的佛坐像即知,完全見不到犍陀羅造像的厚重柔暢衣飾,亦無波浪髮式。肉髻凸起,作大螺狀,剃髮圓面,頰頤豐滿,雙眉以細線刻之,目大而張,嘴唇厚實,唇角帶著古樸微笑,具印度人面部的特徵。身著右袒式僧衣,薄如蟬翼,緊貼身體,曲線畢露,雙肩寬厚,胸肌飽滿,重視身軀豐厚且帶充實渾融的力量感。印度新德里國家博物館藏的彌勒菩薩像,整體重心平均置於雙腳上,然一腳稍帶動勢,身軀則是健壯結實,厚實飽滿;高大挺立的體態,俊美清秀容貌,讓人見其源自印度早期的藥叉像姿態,在風格上雖別於犍陀羅,不過體態及容貌上多少是有關的。犍陀羅與秣菟羅二者風格雖異,然貴霜王朝時二地之間互有來往,在造像上自然是相互影響的。
(2)阿瑪拉瓦提
貴霜王朝勢力雖強,然僅止於印度西北與北部,而在南印度興起的薩塔瓦哈納,開啟了阿瑪拉瓦提雕刻,與犍陀羅、秣菟羅三足鼎立,閃耀天下。南印度是印度本土達羅毗荼文化(Dravidian)的根據地,故薩塔瓦哈納純屬於「印度人的印度」,是印度民族傳統精神的庇護所,故阿瑪拉瓦提造像,不僅沒有犍陀羅那樣的希臘化,反而比秣菟羅更純粹地保留了印度傳統。再者,大乘佛教的倡導者龍樹菩薩終老於阿瑪拉瓦提西北方50公里的龍樹丘,故薩塔瓦哈納晚期的佛教美術,除了繼續繼承早期的傳統,雕製佛傳和佛陀象徵物外,亦受到大乘佛教思想的刺激,從二世紀以來普遍地雕造佛像,例如在龍樹丘遺址入口的一側為佛塔,另一側則為佛立像。再者,今藏於清奈博物館的佛塔圖,約造於二世紀,在佛塔上可見代表佛陀的法輪象徵物等,同時在佛塔上方亦有說法的佛坐像,二者兼有並存,蔚為當地特色。今藏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龍樹丘考古博物館藏三世紀時的佛立像,佛像五官輪廓仍以印度人為依歸,然面橢圓形,肉髻低平,髮作旋螺形,正是三十二相中的「螺髮右旋」;臉頰下巴圓潤豐滿,弓眉秀目,直鼻厚唇,為南印度特有形貌;身軀作圓筒形狀,修長有致且著右袒式僧衣,衣服質地厚重,雖不見身體,然隨著簡潔流暢的陰刻紋線,布滿全身,具十足的體積量感。
貴霜王朝的三大藝術:犍陀羅、秣菟羅、阿瑪拉瓦提,相互融合,亦相互影響,本土的傳統與外來的語彙,不斷攝受汲取,在印度民族的大熔爐中衝撞、融化、結晶、昇華出印度古典主義的審美品味,開啟了印度藝術史上令人驚羨的黃金時代——笈多王朝。
(三)笈多王朝
四世紀初葉,摩揭陀的旃陀羅笈多一世(Candra GuptaI,約320〜330在位),又稱月護王一世,雄才大略,逐步併吞諸小國,開啟笈多紀元,定都於華氏城,史稱王朝。其子沙摩陀羅笈多一世(Samudragupta,約335〜380在位),又稱海濩王,非常英明,征服了北印度全境和中印度大部分,開展了足以媲美阿育王的一統印度,遠近諸國皆來臣服。第三代旃陀羅笈多二世(Candra GuptaII,約380〜415在位),號稱超日王(Vikramaditya),戰勝了西印度的賽族統治者,文治武功盛極一時。然賽建陀笈多(Skandagupta,約455~467在位),王朝內亂外患頻仍,國勢逐漸衰落,各代諸王逐漸退守到摩揭陀一隅,國祚延續到六世紀中葉。印度藝術史上慣稱的古典黃金時代約為三二○至五五○年,之後就是後笈多王朝(約550~650)。
笈多王朝長達二百多年,其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都達於頂峰,此時期名僧輩出,大乘佛教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尤其是無著、世親兄弟,完整地建立了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亦稱唯識派哲學的理論體系。大乘佛教的流行,亦促使佛教美術的發展,逐步達到巔峰。但此時的犍陀羅已失去昔日的光彩,兩大佛教造像中心乃屬秣菟羅與鹿野苑。
1.秣菟羅
秣菟羅造像進入笈多王朝,在造型上融合了早期秣菟羅與犍陀羅的作風,逐步開創出一種新形式的佛像,極受世人矚目。秣菟羅的美術發展,從五世紀起,開始出現修長而又高仰、秀美之勢的佛像,取代了以前深具量感的雄渾強健。修長的四肢,裝飾的衣褶,繁縟的紋雕,填滿的大頭光,揚起了新風格的動勢,形成笈多佛像的典型風格。然而,所謂笈多佛像風格,不止於外在新形式改變,也開始走向印度前所未見的內在精神意涵。此時的佛教已不再是君王唯一的信仰,再加上當時後起的印度教勢力逐漸強盛,促使佛教逐漸走向幽遠、深邃的沉思冥想修行。佛教這種內化深邃趨勢,造成佛像走向更為深思內省,悠然覺悟的生命昇華的造型,如藏於秣菟羅博物館一尊高達220公分的佛立像,即是典型的標準造像。其顏面為印度人,鼻子卻是希臘式,眼神冥想中,螺髮整齊有致,僧衣通肩,且有一道道「U」形衣紋,如流水般,揚起柔順流暢的律動。單薄的僧衣緊貼身體,猶如浸過水,濕潤的半透明般,隱約浮顯全身的輪廓。這種半透明般的濕衣效果,是笈多秣菟羅式樣佛像最典型特徵,故又被稱作「濕衣佛像」。其身後的碩大精美華麗的頭光,中央為蓮花,接著一道道精緻植物紋樣,有序地布滿整個空間,低垂半閉的雙眼,令人見及其內心思惟冥想,緩緩地因內省而昇華開展,宛如正盛開的花朵。
這種笈多佛像造型特有的精緻語彙,令人見到笈多佛像注入了沉思冥想的寧靜精神,使精神成為軀體內的靈魂,外在美轉成精神美,達到高度的協調,成為印度古典藝術最高成就代表。
2.鹿野苑
鹿野苑早在阿育王、貴霜王朝就是著名的佛教聖地,笈多王朝更是佛教美術的一大中心,其風格異於秣菟羅,最大差異在於其造像幾無紋褶,光滑如裸體般,身軀極為柔暢堅實,雙肩及體背不若秣菟羅寬厚,反而表現該地特有纖美優柔之感。最為著名的,就是出土於傑馬勒布爾(Jamalpur),目前印度新德里總統府藏的秣菟羅佛立像,及鹿野苑考古博物館收藏的佛陀初轉法輪坐像,並稱雙璧。此尊佛坐像即是鹿野苑「裸體佛像」的典範,其造型之美,在於初轉法輪印相與其低垂半閉眼簾的交集,以及純淨昇華的體軀與其背後繁複華美的紋飾形成對比。其右上左下的轉法輪印各露三指,右上向外的三指正意味著佛、法、僧三寶,左下的向內三指象徵身、口、意三密;然而三寶、三密皆本於外在之眼、內在之心,故心、眼、手三者的如一如實交集,正是佛陀為眾生初轉法輪的原旨本意。若就整體的造型觀之,結跏趺坐姿與其頭頂正構成穩定的三角形結構,於背後嵌入碩大精彩美麗又繁複精緻的大頭光,正與其前光潔如鏡、透明如水的身軀,成一明顯強烈對比之美,突顯鹿野苑獨特的風格。此坐佛仍穿有通肩僧衣,雕刻手法細膩,讓人感覺到領口、袖口、下襬邊緣若有若無,薄之又薄地完全達至如水浸潤般的透明,毫無滯礙的巧思與技法,堪稱一絕。然而,印度古典黃金時代雕刻,就止於此,其後就難以再現。
3.犍陀羅
貴霜王朝的佛教美術活動中心犍陀羅,在笈多王朝亦有造像活動,不過已大不如前。過往以石雕為主,此時造像已漸漸走向以泥塑為主,其風格仍是希臘化造型。例如豐都基斯坦佛寺遺址(Fondukistan)出土的菩薩坐像,整體洋溢著悠暢柔細的感覺,身軀作「S」形變化,非常柔和。然而手指和腳趾卻顯現稍帶緊張的感覺。髮間飾物是先做好之後,再一一嵌合上去,極為精緻且規整有序。其造型是受到印度笈多王朝式樣的影響。塑像土質較粗,故顯得脆弱些。
二、中亞
中亞美術,即古代稱的西域美術。以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為界,分居於東、西土耳其斯坦兩地的地區美術。其東側的土耳其斯坦,即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側的土耳其斯坦,即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四個共和國。
就美術而言,為順應當地風土與材料等條件,幾乎以雕塑和壁畫為主。在雕塑上,新疆除泥塑外,尚有木雕、鑄銅類造像,西土耳其斯坦有少量的石雕。古代印度開啟的佛教文化及美術,就是通過中亞,沿著絲綢之路,傳進中國,後更開啟了韓國、日本的佛教及其美術。此處的塑像,純粹以泥塑為主,一般以捆綁蘆桿或樹幹等為骨架,加上各肢體的形樣,之後上小釘,或綁以繩索,一步一步地敷以泥塊,塑造成型後,再施色彩或貼上金箔,方才完成一尊尊的塑像。題材除佛、菩薩像外,亦有神將、羅漢,以及當地世俗男女、騎馬等造像,當然也包含當地信仰的神祇,尤其是女神像。
新疆南道、北道絲路上的塑像,由於斯坦因、伯希和、勒柯克、大谷光瑞等人的探險與文物的陸續出土,現已廣為世人所知,但西土耳其斯坦的塑像,就比較不為人知。在粟特(Sogdia)出土有阿娜希達(Anahita)的女神像,特別是布卡全寇夫(Galina Anatolevna Pugachenkova)在烏茲別克斯坦哈勒傑揚(Khalchayan)發掘出一座古代一世紀的宮殿,見證受到希臘影響,而且在內部壁間有著等身大的希臘題材的彩色塑像,除了王族夫婦、騎馬武人、鎧甲武士之外,亦有阿波羅(Apollo)、雅典娜(Athena)、希臘酒神戴奧尼斯(Dionysus)的侍者賽特洛斯(Satyr)等,令人見及古代希臘、大夏式美術製作,其後亦可見到以犍陀羅雕刻為雛型的塑像,故亦有人稱為阿姆河(Oxus)風格,如烏茲別克斯坦出土的菩薩立像、菩薩像,著實是希臘、大夏的式樣風味;同地的釋迦牟尼佛龕像、佛傳圖,以及土庫曼斯坦的佛坐像、塔吉克斯坦的佛坐像等,即是源於犍陀羅雕像的式樣與風格。
三、中國
中國的造像,尤其是佛教雕刻,幾為西方人所開啟,再加上佛教的傳播自西而來,因而佛教造像的風格,幾乎源自西方的犍陀羅式樣。近十餘年來,已有不少學者展開更多元的來源探索。由於中國五十餘年來的考古發掘,出土不少過去不為人知的造像遺址與文物,例如江蘇連雲港的摩崖造像、四川樂山麻浩崖墓墓門上的佛坐像、四川地區為主的搖錢樹座佛像,以及不少三國(220~280)兩晉(265~420)銅鏡上的各類神佛像等,在在改寫過往研究的結論與觀點,其後,出現了更為強而有力的南傳佛教傳播路線之說。
然而,自五胡十六國(303~439)起,西域來的造像興盛,尤其是河西武威一帶興起的北涼(397~439),堪稱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的奠基者。北魏(386~534)在山西大同的雲岡石窟,其造像、造窟手法,幾乎就是直接移植北涼而來,使北涼西域造像成為中國初期造像式樣的藍本。
北涼造像,在天梯山、馬蹄寺、金塔寺、文殊山及敦煌莫高窟第275窟等,仍可見留傳至今的西域造像式樣。方碩寬廣的五官面相,是西域首現的標誌。上身袒、下著胡服裙裳、厚重量感的軀體表現等,尤其飛天造型,呈「U」形、結實豐碩身軀的飛翔之姿,極易辨識出西域風味。就石窟而言,中心柱窟的四面造像或龕像等,亦是常見此規則的範例。
(一)東漢兩晉
中國初期造像,始終不明,過往幾乎止於史冊紀錄與傳聞。東漢明帝永平八年(65),帝退還楚王英贖罪縑帛,以布施沙門,得知當時已有僧人、寺院。永平十年(67)蔡歆與竺法蘭、攝摩騰攜佛像與佛經到洛陽,於是在雍西門建白馬寺,其後桓帝永壽元年(155)於宮中立浮屠、老子之祠,並設老子像。其中最可信的,依《後漢書‧陶謙傳》及《三國志‧吳志‧劉繇傳》載,興平二年(195)笮融任下邳相,大興浮屠祠,造銅像,黃金塗身,衣以錦彩。浮屠祠上懸垂有九層銅盤,下為重疊樓閣,可容三千人,而且皆悉讀誦佛經。佛像之事可見於《後漢書‧陶謙傳》及《三國志‧吳志‧劉繇傳》。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皆有這類建寺造佛傳聞,直至二十世紀,國外有心人士致力於中土造像探究,遂令世人逐漸明白中土亦有造像的事實,如傳陝西省三原縣出土,四世紀上半葉左右,現藏於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的金銅菩薩立像;河北省石家莊出土,美國哈佛藝術博物館藏的十六國金銅釋迦牟尼佛坐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所藏的,首件具有年代題記的後趙建武四年(338)金銅佛坐像,以及北京故宮藏的西晉(265~316)前後金銅菩薩立像等。
近年有關佛教造像圖錄相繼出版,使世人有機會見到相繼出土的東漢(25~220)初期考古實例,如約成於延熹年間(158~167)四川樂山麻浩崖墓佛坐像,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佛像範例;彭山崖墓亦出土一佛二菩薩的搖錢樹座,亦是東漢晚期遺物;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亦收藏一棵既精緻又精美的大型搖錢樹,在其樹幹枝節上,可見一節一節的佛像;湖北武昌出土三國吳永安五年(262)的鎏金佛像銅飾、江蘇南京出土三國吳青瓷羽人紋佛飾壺,以及江蘇吳縣、金壇等出土極多兩晉期間青瓷佛飾堆塑罐,此種罐就是民間俗稱之魂瓶,或骨灰罈。至此,東漢佛教傳入中土初期即有造像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後江蘇連雲港孔望山大量佛教刻像及銅鏡的佛頭造像,就更自不待言了。中國初期造像混雜了戰國(476~221 BCE)以來的當地神仙信仰,且在考古墓葬中,說明了當時造像信仰主流應是在家信仰,並非出家沙門,才會有自墓葬中出土的佛像遺物。
(二)南北朝
晉室南渡,北方被五胡所占,共立十六國,即史稱的五胡十六國。其中鮮卑族拓跋氏於四世紀末逐漸得勢,於登國元年(386)稱魏。相對南方的晉朝武將劉裕滅後秦(384~417),接受禪讓,於永初元年(420)篡晉稱帝為宋。自此南北對峙,至隋統一(589)止,期間約有一百五十至二百年,即史稱的南北朝時代。
南北朝時代是佛教及造像藝術的重要開展期,而南朝、北朝各有獨特的發展及特色,然其變異有三:
1.佛教發展的重要關鍵者鳩摩羅什,於後秦弘始三年(401)到長安(今陝西西安),即開始弘揚當時興盛的印度龍樹學派中觀思想,對中土影響極大,史稱兩晉為「格義時代」,而羅什之後為「學派時代」。事實上此時期並非僅於學派的佛教研究,同時佛教的宗派也開始鞏固其基礎。特別是當時南北分立,教學相競,各自開展獨特教風。南北學風不同,相對的佛像的式樣、風格等亦不同,為探討南北朝造像差異的重要根源。
2.此時的北朝,有北魏太武帝(423~452在位)和北周武帝(560~578在位)的兩次廢佛,促使北魏後的中土佛教性格更為堅強,亦促使對立的中土佛教界走向折衷,漸漸褪去了外來佛教的性格,開始萌發自身的獨特性。這源自廢佛的中土佛教之歷練與成就,對其造像,尤其是雕刻式樣,影響甚大。
3.中土佛教源自印度,但並非直接傳入,北傳路線經由印度西北地區的西域各國,南傳路線則由海上絲路而來。當時因北朝與西域交流頻繁,造像具豐富的國際色彩,而南朝少與西域交通,故造像繼承漢家傳統,民族色彩較重,因而發展出與北朝不同的式樣風格。
南朝造像據說完成於東晉的戴逵、戴顒父子,史稱「二戴像制」。《晉書》記載陸逵十幾歲時便參與瓦官寺的作畫,受到讚賞,《歷代名畫記》卷五更詳述其製作佛像過程,為使造像生動,甚至還曾藏在帷幕中細聽他人議論,然後潛心用功,終於三年有成,雕出受人讚賞的無量壽佛大像。戴逵的造像,已逐漸去除印度造像法的約束,不但走出獨自的傳統品味,更採用中土傳統藝術的漆藝手法,製作脫胎的「夾紵行像」,便於四月初八的佛誕遊行。從《歷代名畫記》亦可得知戴逵精於金銅佛像之製作。日本東京永青文庫藏的劉宋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金銅佛坐像、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的劉宋元嘉二十八年(451)金銅佛坐像,是目前所知南朝宋(420~479)著名的金銅像。以戴逵活躍於晉宋期間來看,此二尊的造像形式、風格,應與二戴像制是分不開的。
南朝齊(479~502)、梁(502~557),精通律學的僧祐是位罕見的專精造像藝術僧人。僧祐除有《出三藏記集》、《弘明集》、《釋迦譜》等重要著作外,其造像成就更值一提,僧祐有「目準心計,尺寸無爽」的造像才華,依《高僧傳》,造有光宅、攝山大像、剡縣石佛等。光宅寺原是梁武帝(502~549在位)邸第,施捨為寺,僧祐造光宅丈八無量壽金銅佛,屬國家級的大佛。據說宋明帝(465~472在位)時佛像四鑄不成,到梁天監八年(509)沙門法悅和智清懇請再鑄,即請僧祐主持,佛像竟一鑄而成。攝山大像即今南京棲霞山千佛崖無量壽龕像。此大像雖經後代重修已失原樣,但從其高大的氣勢,亦略可窺知當時原貌。剡縣石佛位於今浙江新昌縣西南的明山大佛寺,舊稱寶相寺,此石佛最初由僧護發願,於南齊建武年間(494~498)動工,然多年僅止於佛面而已,不久因僧護病故而停止。後有沙門僧淑遣工為之,卻又因財力不足而迫中止。梁天監六年梁武帝遂特請僧祐專任像事,約耗時三年餘完成。高有13.23公尺,座高2.4公尺,為一巨大造像。
南朝雖有戴氏父子及僧祐等造像名手,具漢家千年傳統特色,惜遺留的造像範例缺少,不過在一九五○年代四川成都萬佛寺造像的出土,多少令人得以了解南朝造像式樣別於北朝特色的形制之美。
相對於南朝造像遺存不足,北朝卻是豐富異常,不僅數量多,而且遍布廣,可謂是造像的盛世,尤其大型石窟的開鑿,更是首屈一指,主因為北朝皇族對佛教的重視。北朝雖由胡人統治,千年的漢文明卻不因胡人治國而喪失色彩,反而成為胡人積極吸收外來佛教的墊腳石。北魏基於漢家傳統,全無包袱地擁抱佛教,大力推行造窟、造寺,故有雲岡、敦煌、龍門、麥積山等石窟的誕生。當時國力強盛,通達西域的交通不但促使造像深具國際色彩,更強烈反映西域各國風情,成為今天探究東西藝術、文明交流的多元重要課題。這一點,實與南朝有極大差異之處。
北魏造像量豐,且時間長達約有一世紀之久,故式樣風格,五世紀以曇曜造立的五大佛為主,即「曇曜五窟」。綜觀之,因受到西域造像式樣影響,軀體顯現圓雕形樣,強勁有力的起伏變化,而相貌方正豐厚,及巨大量塊雄偉厚實的體軀感,皆是其特徵。衣紋上,例如雲岡石窟第20窟佛坐像的兩條隆起衣褶線,成為當時,甚至其後的金銅、石佛像的基本標誌。
因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的漢化政策,促使雲岡石窟本深具西域的造像式樣逐漸漢化,即「褒衣博帶」的流行,開展其後的龍門石窟造像式樣。換言之,太和十八年(494)後,即北魏後半期,開始有漢服帝像的佛像製作,見不到前期印度或西域的服飾。相對前期充滿厚重量感的身軀亦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面長清秀的相貌出現。
簡言之,六世紀上半葉的龍門石窟造像,逐漸顯露漢家傳統,除面長清秀外,衣褶的統整與表現,亦值得一提。首先是北方嚴謹的味道漸少,強勁有力的衣紋隆起線,逐漸轉化成平板重疊的襞褶表現手法,衣裾、衣袖亦作相當距離的離心式統整。整體看來,雖仍保有北方的嚴謹與強烈度,卻產生顯著質的變化,洗練有勁的紋理,已逐漸浮現出漢傳統細緻的線性情感風味,成為其後北魏末到北齊(550~577)、北周(557~581)時期的流行代言。細看這時期常見的黃花石、白石造像,或表面極度加工潤飾的小石像,皆可見到這種細緻又瀟灑的式樣情愫。
北魏前期造像極富變化且強勁有力的量塊感表現,自北魏後期逐漸走向平面性的浮雕手法。再者,前期具西方圓雕風味的造像,因當時偏於摩崖雕刻所賦予的必然條件,故而不得不傾向於「浮雕的式樣」了。此時的摩崖或石窟壁面、大碑像等,皆可發現已是浮雕造像多於圓雕。這樣浮雕式的造像表現,使原來深具前後遠近,與具立體性的三次元空間視覺,轉變成直接的「縱與橫」的二次元空間限度,明顯地縮短視覺的感受。故此時造像走向左右相稱的表現,衣袖和衣裾的末端常常作出向兩側大大舒張的處理。這樣的手法,已不止於摩崖刻像,而是圓雕式的金銅佛、石佛等,亦被齊一了。
浮雕式的正面性觀照視覺之美,因北齊、北周時期的「鮮卑化」又為之一變,使立體圓雕逐漸興起,進而相融互攝,開始出現柔和歡喜表情的造像。事實上,這在北魏末期已開始,其後更加洗練。顏面賦予了圓潤柔和韻味,著透明可見軀體般的薄衣,整體衣紋精緻細微的薄刻,簡直薄到不可再薄,令人有如直接觸及身軀般的感覺,又是意想不到的一變。近二十年來大量青州造像的出土,正是此風格的原味。
北朝的造像,除了大量佛像,亦有不少的道教像。北魏太武帝的廢佛,與對道教信仰的崇拜有關,再加上北周武帝亦崇尚道法,故北朝亦盛行道教像。有兩種造像形式:一、道教與佛教合併的雙教碑像,以北魏始興二年(424)魏文朗造像碑最早受人矚目,另一件是獨立的道教造像碑,以北魏太和二年(478)劉氏造像碑最早。一般而言,北朝道像以陝西鄜縣出土,及耀縣藥王山博物館收藏為是。
(三)隋唐五代
中國造像藝術,前有北魏,後有隋(581~618)唐(618~907),堪稱造像史上的黃金時代。隋唐造像之盛,除了奠定於南北朝的基礎外,加上國力的強盛,遣人直赴印度攜取佛像圖樣粉本,更是決定性的關鍵,期間出現了不少的重要僧人和雕刻家,更不須贅言。
七世紀上半葉唐代玄奘自天竺(今印度)取經而回,不僅造就譯經院的開啟,在造像上亦有極大影響。從印度隨佛經帶回的七尊佛像,其中以旃檀刻的優填王像,不僅大盛於當時兩京,各地石窟亦模仿之,光在龍門石窟就有四十二處遺蹟,造像七十餘尊。再者,玄奘譯的《法住記》中詳述十六羅漢形跡和各自眷屬。有言阿羅漢受釋迦佛囑託,在釋迦滅度後護持佛法,不入涅槃,常在世間教化眾生。自此羅漢像流布中國,從十六羅漢增列到十八羅漢,其中二尊羅漢之名不定,直至清代(1644~1911)時才定為降龍、伏虎二尊者。再者,五百羅漢在宋代(960~1279)即已出現,其尊名是由南宋紹興四年(1134)工部員外郎高道素費盡心力,於《大藏經》中輯出五百名號。
七世紀下半葉,義淨又自西天竺取經而回,帶回摩伽陀國金剛座真容像一鋪,時,武則天(684~705在位)特在上東門外親迎。這鋪真容像曾在兩京翻刻流行,其原始圖樣與武則天長安年間(701~705)七寶台三尊像浮雕類似,這類的三尊式樣可見於萬歲通天年間(696)開鑿於四川廣元千佛崖石窟第535窟蓮花洞中。廣元為武則天故鄉,故蓮華洞造像可知是直接源於兩京的。
因唐代國力強盛,有王玄策、李義表等人四次訪印度,並帶回大量印度造像粉本,期間還有雕塑名家隨之前往,因此攜回的模寫粉本極為精妙。貞觀十七年(643)隨著出訪的名家宋法智,描寫帶回摩揭陀國的菩提瑞像就一直流傳於兩京。麟德元年(664)玄奘臨坐化前,高宗(649~683在位)還請宋法智在嘉壽殿前豎立「菩提像骨」。當時和宋法智齊名的名家,尚有吳智敏、韓伯通、竇弘果等。盛唐(712~756)之後,就是史上著名的楊惠之了。據言塑壁技術和千手千眼菩薩形象,皆由其創始。
塑壁即在牆壁上堆出山巒勝景,其間穿插人物等等,顯示石窟的須彌山雕塑。今山西一帶許多明清寺院中,眾多的羅漢或各類神像及人物表現上,就採取了唐代楊惠之的塑壁手法。千手千眼菩薩自楊惠之首創以來,粉本式樣很快地流傳於民間工匠中。晚唐(846~907)五代(907~960)後,佛教寺院盛行蓋大悲殿,殿內的大悲像,原始圖樣即有可能源於楊惠之。
隋代造像基本上造型優美,形制典雅,彰顯當代貴族持奉念佛的趣味。從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的大型隋開皇五年(585)阿彌陀佛立像來看,軀體具有相當的圓雕味,不過下半身扁平,再加上柔和的眼鼻、流利整齊的線式衣紋刻製,倒是北齊的特色。一九七四年西安八里村出土的開皇四年董欽造阿彌陀佛像,以及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的開皇十三年范氏造阿彌陀佛像等,皆同於前述巨像的風味,其姿態極具柔軟性,整體透顯著纖細優美的趣味,這樣的趣味就是南北朝形式美的遺風,隋代再逐漸增加其柔軟性,二者相互融合,又獨具華麗貴族的高雅造型之美。
隋滅唐代興起,雕刻式樣並未急速轉變,不過因初唐存留的造像範例極少,若從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藏貞觀十三年(639)的馬周造佛坐像來看,確是當時長安的造像,不過與隋代同樣的佛像相比,可發現軀體各部均衡整齊,整體造型自然圓潤,就寫實性而言,是較其前更加進步。因此,初唐遺例雖少,然而以體勢端莊,氣宇昂軒的角度來看,即可探知初唐在物體觸覺的把握與像體的適用度表現,已達成熟的境界。
唐代雕刻重寫實性,但在佛像的製作上,並不僅於寫實而已,還賦予崇高、超凡存在感的宗教價值。唐代佛教雕刻被譽為「黃金時代」,就是建構在寫實和精神理想的融合上,如初唐(618~712)龍門石窟奉先寺盧舍那佛像,正道出唐代佛教雕刻的根本之道。龍門石窟從隋代到唐代的各種造像,正如實地顯現這類式樣形成的交融過程。自隋至盛唐的一百年間,確實帶來了新鮮的造像能量,同時也快速地形成以盛唐為代表的唐代式樣。
盛唐雕刻以寶慶寺派的石佛群為代表。此群龕像原是在長安城光宅寺,後被移出嵌進西安寶慶寺佛殿的壁上,因此名為寶慶寺派。大致分二類,一佛二菩薩龕像和十一面觀音菩薩龕像,總數有三十多鋪,其中十九鋪在日本。在一些銘記中可見到,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藏的長安三年(703)十一面觀音菩薩龕像、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的長安四年姚元景造一佛二菩薩龕像,以及日本東京文化廳藏的開元十二年(724)楊思勗等造彌勒三尊龕像。長安年間的造像,令人想到的是在初唐至盛唐間完成,雖說有相當的變化,但總讓人覺得是習慣性的手法,有些墨守成規。開元年間(713~741)的造像,雖身形豐厚些,但整體造型掌握極好,換言之,初唐造像風格延續到盛唐。美國費城賓州大學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收藏的神龍二年(706)觀音菩薩像,可謂是盛唐中造像的佳作。整體健壯又豐美的軀體,眼、鼻、顏面與高挺直立的氣勢等種種相好,顯示出盛唐造型量體與結構的優美語彙。不過,瓔珞、衣紋等雕刻較淺,略顯形式化,下半身的重量令人感到有些不足。
盛唐後期,即開元之後的造像,漸漸出現過渡性的豐厚形樣。事實上,盛唐的俑,或壁畫人物,即源自當時世俗寫實手法的表現,有著視覺美感的品味。不過當世俗性的寫實失去了精神性的理想,尤其下半身表現又過度豐厚時,優美明快的造型語彙就不再產生,只有趨向頹勢。就宗教美術的生命而言,顯得極度不當。
盛唐玄宗時期(712~756在位),從印度傳來了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等真言教的祖師像,在漸漸衰退的盛唐雕刻中,出現氣質優美、格調高雅、造型相好的密教雕刻作品,一掃盛唐後期的衰退,增添此時期造像藝術的光彩。例如,今藏於日本奈良法隆寺的白檀木九面觀音菩薩像、西安碑林博物館安國寺遺址出土的虛空藏菩薩像,以及著名的河南洛陽龍門石窟擂鼓台南洞菩提瑞像等即是。
五代十國(907~979)雖政局動盪,不過佛、道二教皆盛,造像亦豐富。此時盛行僧人造經,匠人造像,釋、道題材已與民間習俗混雜兼用,活躍的雕塑家,大多佛、道皆通。重要的是,出現前所罕見的造像,如熾盛光佛、九曜二十八宿等像,以及一直流傳至今的地藏菩薩像等。
(四)吐蕃
藏傳佛教的雕塑造像歷史悠久,富有自己的地域和民族特徵,同時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又和周邊地區的佛教造像藝術有過許多交流融會,經歷了幾個造像風格演變的過程。
按照一般的說法,佛教在西藏的傳播從一開始就和佛陀的兩尊金銅造像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七世紀上半葉,吐蕃王朝(7~9世紀)的創建者松贊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650在位)迎娶尼泊爾光胄王(Amsuvarman,605~629在位)的女兒赤尊公主為妃。赤尊公主帶的嫁妝,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尊釋迦牟尼八歲身量的銅像,藏語稱為覺臥米覺多吉(jo bo mi bskyod rdo rje),譯成漢文即是不動金剛佛像。後松贊干布又迎娶唐太宗(626~649在位)的女兒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帶到拉薩的嫁妝,其中也有一尊釋迦牟尼十二歲身量的銅像,藏語稱為覺臥仁波且(jo bo rin po che)或者覺臥釋迦牟尼(jo bo shakya mu ne)。為供奉二位公主所帶來的佛像,赤尊公主在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協助下建立羊土神變寺(ra sa ‘phrul pa’i gtsug lag khang)。拉薩(lha sa)地名就是從該寺寺名的前二字邏些(ra sa)音而來,後稱為大昭寺(lha ldan gtsug lag khang),寺內供奉覺臥米覺多吉像。文成公主建惹莫且寺(ra mo che gtsug lag khang),後稱為小昭寺,寺內供奉覺臥釋迦牟尼像。據傳松贊干布的孫子芒松芒贊時期(mang srong mang btsan,650~676在位),吐蕃與唐朝發生戰爭,吐蕃擔心唐朝會取回覺臥釋迦牟尼像,就將其移藏至大昭寺中,並在外面砌牆遮蔽。後來唐朝的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赤德祖贊(khri lde gtsug btsan,704~755在位),金城公主到拉薩後,努力尋找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覺臥釋迦牟尼像,最後從大昭寺隱藏的地方將覺臥釋迦牟尼像迎請出來,安置在大昭寺的正殿中央,又把赤尊公主帶來的覺臥米覺多吉像迎到小昭寺中供奉。此最著名的兩尊西藏佛像就因此被掉換了位置。
此兩尊金銅佛像至今仍保存在拉薩的大昭寺和小昭寺中,是最受藏族人崇拜的兩尊佛像,同時也是聯繫西藏歷史上重大事件最為密切的金銅佛像。後來有許多熱心的佛教徒和富有的施主,甚至著名的佛教大師,為這兩尊佛像多次貼金裝飾,添加黃金和寶石的頭冠和衣飾等。例如元代(1271~1368)拉薩的地方首領蔡巴萬戶長和阿里的土王等人曾出資維修大昭寺,用25,000公斤銅和500兩黃金為佛殿建造金頂;格魯派(dge lugs pa)的創始人宗喀巴(tsong kha pa)在一四○八年年底曾為覺臥釋迦牟尼像奉獻新製佛冠和佛衣,一四○九年正月創辦拉薩祈願大法會,法會期間每天為覺臥佛像的面容塗金,在初八和十五兩天則為覺臥佛像的全身塗金。之後,宗喀巴創建甘丹寺(dga’ ldan dgon pa),在西藏的歷史上占有統治地位的格魯派由此形成。在五世達賴喇嘛、七世達賴喇嘛和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都對大昭寺進行大規模的維修,直到現在,大昭寺的釋迦牟尼像和不動金剛佛像每年都塗金,隆重供拜。儘管近年有學者發現大昭寺的覺臥佛像底座的題款與以上說法不同(題款稱這尊覺臥像是在五世達賴喇嘛時期鑄造),但十一至十四世紀的藏文史籍,即詳細記載大昭寺的建寺過程和覺臥佛像的故事,因此並不能依據這一題款推論,可能的解釋是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建造的覺臥佛像,替代了此前的覺臥佛像,而在廣大藏傳佛教的信徒心中,覺臥佛像是文成公主在松贊干布時期帶來拉薩的史實最為重要,至於後來覺臥佛像的變化或者被替換,是不必特別加以注意的。不辭千里高原跋涉的艱苦,不畏生命危險,信徒們甚至磕著等身的長頭到拉薩朝聖,他們一生中一項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繞行大昭寺,也就等於繞行和禮拜覺臥釋迦牟尼和覺臥米覺多吉。拉薩城中最著名的八角街和林廓路,即千百年來信徒們朝禮此兩尊金銅佛像之路。每天早晚兩次繞行大昭寺的隊伍,常在萬人以上,浩浩蕩蕩的隊伍肅穆莊嚴,使見到的人也強烈地感到震撼。兩尊金銅佛像使一個地區的政治和宗教歷史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在佛教史上是十分罕見的。
藏族的金銅鑄造工藝在佛教傳入西藏前就有長期的歷史。據藏文史料記載,在松贊干布的二十七世祖止貢贊普時代(gri gum btsan po),就能製造多種刀劍武器,甚至銅棺。六四六年,唐太宗征討高麗返回長安,松贊干布遣使奉獻金鵝,祝賀唐太宗凱旋。「其金鵝黃金鑄成,其高七尺,中可實酒三斛。」唐代以十斗為一斛,吐蕃所獻的金鵝可裝酒數百公斤,可見其工藝非比尋常。唐玄宗時,吐蕃多次進獻金鵝盤盞和金銀器玩,有時一次甚達數百件,而且形制奇異,工藝精絕,唐玄宗還下令在宮門陳列,讓百官參觀,可見吐蕃的金銅鑄造工藝本來就有很高的水準,因此在佛教傳入後用來鑄造金銅佛像,本應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儘管由於朗達瑪(glang dar ma,841~846在位)滅佛和吐蕃王朝崩潰後的長期戰亂,吐蕃王朝時期西藏的佛教造像遺留下來的很少,但從文獻上還可看到吐蕃王朝時期佛教造像的發展,當時應當有大批印度、尼泊爾、中亞和唐朝的藝術家受聘在西藏進行早期佛殿和寺院的裝飾藝術創作和造佛。
藏文古籍《拔協》(sba bzhed)載,贊普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在位)興建桑耶寺(bsam yas gtsug lag khang)佛像時說:
「匠師問:『佛像是塑成印度式還是塑成漢地式的呢?』
大師:『佛陀降生在印度,所以塑成印度式的吧!』
贊普:『大師,我希望讓吐蕃喜歡黑業(黑苯教)的人們,對佛法生起信仰。所以無論如何,也請把佛像塑成吐蕃的式樣!』
大師:『那麼把全體吐蕃民眾召集起來,就塑成吐蕃人模樣的佛像吧!』
於是從召集來的吐蕃民眾中,挑選出最英俊的男子枯達擦,依其模樣塑造了二臂聖觀音;挑出最美麗的女子覺若妃子布瓊與覺若妃子拉布門,左邊依覺若妃子布瓊模樣,塑造光明天女像,右邊依覺若妃子拉布門塑造救度母像。照塔桑達勒的模樣,在右邊塑造了六字觀音像(四臂聖觀音);照孟耶高的模樣,塑造了聖馬鳴菩薩為守門者。」
這說明赤松德贊興建桑耶寺之時,已經出現了西藏本地的佛教造像風格。從桑耶寺建成到朗達瑪滅佛的六十多年間,是西藏佛教急速發展的重要時期,贊普赤德松贊(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在位)和熱巴巾(ral pa can,本名赤祖德贊khri gtsug lde btsan,815~841在位)都興建過許多寺院,佛教造像也有了很大的發展。
在金銅造像發展的同時,吐蕃王朝石刻造像和泥塑造像的工藝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遺留至今的有拉薩查拉路普石窟(brag-lha klu-phug)和昌都鹽井吐蕃石刻造像,桑耶寺的泥塑造像和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開鑿的洞窟泥塑造像等。
對於吐蕃王朝西藏的金銅造像,出自十六世紀噶舉派的活佛、西藏著名造像大師白瑪噶波(pad ma dkar po)的藏文手稿《鑒別青銅佛像論‧心願口飾》(li ma brtag pa’i rab byed smra ‘dod pa’i kha rgyan),詳載了西藏佛像雕塑中的各種藝術風格和運用的合金材料。他把吐蕃王朝時期的金銅佛像分為三個時期:
1.松贊干布開始的早期法王,主要用紅琍瑪(響銅)製造,佛像面部飽滿,臉部的上部比下部略大,表情愉悅,臉微長,鼻子妙好,眼睛修長,上下唇端麗,身體偉岸,手腳柔軟,衣褶小,整體雕塑造型精美,構圖準確。法座為單排或雙排蓮瓣組成,但有的佛像既無寶座,也無坐墊。佛像身披大氅,足蹬靴,顯示西藏俗人的形象。佛像或鍍金、或用樹脂、或油脂塗光,或根本不塗任何東西。
2.赤松德贊時期的佛像大量使用紫琍瑪製作,與以前製作的佛像相比,面形粗短,手指造型略欠精美。佛像表面敷有樹脂或油脂,鑲嵌設色,底部邊緣銜接不很完滿。大多數佛像都帶有三葉冠;法王塑像無頭巾,髮飾懸垂於肩部兩側。有的鍍金(敷冷金),有的根本不敷任何脂液。
3.熱巴巾時期所造與印度(中部)雕塑家創作的塑像相同,均用白琍瑪為胎澆鑄。不同之處是面形較小,眼睛鑲嵌有白銀和紅銅,鑲嵌技藝高超。塑像造型優美,有三葉冠裝飾;另桑塘瑪佛像(zangs thang ma)的特點是以白銀為眼,紫銅為唇。
(五)宋元明清
北宋(960~1127)佛教造像為之一變,佛、道、儒皆盛,可謂是三家共生又互攝的時代。宋太祖(960~976在位)建國之初,即廣建佛寺、道觀,而且歷代帝王皆相繼營建。太祖開寶二年(969)五月囤兵於河北正定,開寶四年下詔於隋代(581~618)龍藏寺(今隆興寺)內興建大悲閣,並鑄造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高約22公尺,全身塗金,是目前中國現存最大銅鑄觀音像,其樣式依唐伽梵達摩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儀軌,相傳是唐代楊惠之首創。此像巨大,分七段鑄造,太祖曾三次親臨視察,可見皇室對佛教崇信的程度。因此,宋代各地始盛行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像,例如今天在陝北、四川、浙江等地的宋代石窟中皆可見。
宋時的遼(907~1125)、金(1115~1234)、西夏(1032~1227),可謂是以佛教興國,以佛教滅國,因而佛教特盛,建寺造像風氣不墜。山西大同的上、下華嚴寺造像是遼代代表,碩大健美的體軀,寬厚重實的肩背,婀娜曲婉的體態,基於盛唐的體式且更勝一籌的優美獨特造型,堪稱中土造像的極致。另,天津薊縣獨樂寺、遼寧義縣奉國寺、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即應縣木塔),都可見大型又堅實體態的造像。
一一一五年,完顏阿骨打滅遼建金,前後一百二十年間,其代表為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寶殿內正中佛壇為毗盧遮那佛和四方佛,佛兩側均有弟子及脇侍菩薩等,整體莊嚴凝重,氣勢宏偉。因唐末五代的戰亂,令人對護法天神的信仰倍增。遼、金崇佛又尚武功,故雕造極度威武,神采奕奕的各種護法天神像,令人激賞,亦為藏家所識。五台山佛光寺文殊殿建於金天會十五年(1137),殿內彩塑一鋪七尊,主尊騎獅文殊菩薩像,以及兩側脇侍菩薩和供養人像,形態有力、端莊。殿內塑像比例適當優美,裝飾彩繪繁縟華麗,塑造手法有區域性特有的色彩。簡言之,遼金造像繼承唐宋精美式樣,並加上新思手法,造就佛教題材、式樣、內容的多樣化與趣味,其品味實不遜於唐宋。
元、明、清三代,傳統的佛教造像,已被儒、道二教平分了,尤元代道教興盛,其因在於金代興起的全真教弟子丘處機為元太祖(1206~1227在位)所器重,造成元大都全城布滿金碧輝煌的道觀,其數竟達五十二宮、七十觀。全真教創始人王重陽,主張釋、道、儒三教合一,以三教圓通,識心見性,獨全其真為宗旨,其後源遠流長,遍布全國各地,至今甚至在海外許多地區仍極為盛行。
宋元以後,佛教造像題材式樣不斷地變化,山西、四川兩地是保存明清寺院和石窟最多之處。山西因乾燥少雨,戰亂少,故保存的佛像又多又好,各類彩塑和前代遺留下來的完整發展系統,形成非常珍貴且十分值得探究的課題。元、明、清的十八羅漢、五百羅漢,著重人物性格的刻劃,特別是富情節性的懸塑,看似隨意率性,實則更為貼近人間生活,呈現現世人們心靈的虔信本質,如實體現世間生活的本意、生命企求的本懷。群雕的情結構思,已不僅在佛教故事與義理中,也開始自然地融匯了民間戲曲、工藝以及傳統的裝飾趣味,使佛教藝術更加群像化、世俗化。
(六)後弘期
藏傳佛教後弘期開始以後的金銅造像,有兩種風格:一種是隨著「上路弘法」和阿底峽入藏而興盛起來,受印度喀什米爾風格影響的造像,藏文文書稱為「噶當琍瑪佛像」。據說這些造像用天然銅混以金銀做成的合金和紫琍瑪及花琍瑪做原料鑄造,工藝十分精美。由於在噶當派的主寺熱振寺(rwa sgreng dgon pa)供奉許多這種佛像,故稱為「噶當琍瑪佛像」;另一種是隨著「下路弘法」而來的,受漢地和中亞造像風格影響的佛像。下路弘法的發源地青海河湟地區的唃廝羅政權為藏族部落所建立,盛行藏傳佛教,曾經在其都城青唐城(今西寧)興建廣2~3公里的大寺廟,造大佛像,以黃金塗身,並建十三層高的佛塔守護大佛像。
元代是西藏金銅佛像藝術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由於元朝統一了西藏並且扶植薩迦派(sa skya pa)首領管理全國的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的行政,因此薩迦政權能夠集中西藏各個萬戶的力量興建如薩迦南寺大殿如此巨大的佛殿,並得到元朝皇室給予大量珍貴金屬的物質條件下,鑄造出精美大型的金銅造像。薩迦寺(sa skya dgon pa)八思巴(’phags pa)為紀念薩迦班智達(sa skya pan di ta)而建造巨大的釋迦牟尼鍍金銅像,帶有精美的背光以及大量的本尊銅像和祖師銅像,仍留存至今;還有夏魯寺(zhwa lu dgon pa)的金銅造像,亦是此時期西藏金銅造像的代表。八思巴於一二六九年帶到大都的工匠中,有著名的鑄造銅像大師尼泊爾阿尼哥(Araniko)等二十四人。阿尼哥因造像的技藝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寵任,在朝任官數十年。阿尼哥的兒子阿僧哥(Asanga)及弟子劉元也因鑄造佛像而名重於當時。
阿尼哥帶來的尼泊爾藝術和藏傳佛教及漢地藝術,在元朝宮廷逐漸走向融合,逐步形成了一支具有濃烈漢族特色的藏傳佛教藝術創作流派,對後來明清時期宮廷和西藏本地的藏傳佛教藝術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據《元代畫塑記》等文獻記載,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命宣政院院使也延請阿僧哥主持塑造大聖壽萬安寺內五間殿、八角樓的四座佛像,並稟明帝師搠思哥斡節兒八哈失塑造。另外還塑造大小佛像一百四十尊,其中西南北角樓塑麻曷葛剌等十五尊,東西角樓塑麻曷葛剌等十五尊。延祐七年(1320),又令塑工張提舉和畫工尚提舉二人,率眾工匠在興和路的寺院西南角樓內塑馬哈哥剌佛(Maha kala)及伴繞神像,畫十護法神。《元代畫塑記》還記載了塑造和繪製這些藏式佛像所用的西藏的顏料和材料。元代在宮廷中建造的藏式佛像,被稱為「西天梵像」;杭州飛來峰的藏傳佛教石刻造像則代表了西夏(1032~1227)的藏式佛教造像藝術和漢地造像藝術的融合。
明朝前期藏傳佛教金銅造像,有在南京和北京製作的永樂琍瑪佛像,實際上其製作年代是從永樂(1403~1424)延續到宣德(1426~1435)年間。此期間在明朝宮廷中有許多從甘肅、青海藏族地區來的藏族僧人和工匠,如著名的明成祖(1402~1424在位)派往西藏迎請宗喀巴大師的使者侯顯,就是出身於甘南藏區的藏族人,而南京雕版印刷的木刻版藏文大藏經,也是由這些藏族工匠完成的。所以永樂青銅造像應當是由藏、漢工匠在南京和北京共同完成的,永樂銅像正反映出藏漢造像藝術融合的風格。由於永樂琍瑪銅像和法器製作精美,適於作為禮品賞賜和進貢,所以有不少永樂琍瑪佛像是在明代由皇帝賞賜給西藏的高僧和寺院,到清代時又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西藏的宗教領袖,作為貢品進獻給清朝皇帝。因此在清朝宮廷中有不少的永樂琍瑪佛像,甚至還有一些流落到民間。
比永樂銅像稍晚的西藏的青銅造像,來烏群巴琍瑪佛像(sle’u chung pa li ma,清朝宮廷中稱為流崇幹琍瑪。流崇幹即藏文sle’u chung gi,意為來烏群巴),在拉薩市的柳梧地方發展起來的。
清代藏傳佛教的金銅佛像和泥塑佛像數量很多,留存至今的當以十萬計數。依照製作地點區分,主要有以下幾類:
1.清朝宮廷造像:
康熙三十六年(1697)正式設立中正殿念經處,專管宮中藏傳佛教事務,其職責之一就是鑄造佛像。乾隆年間(1736~1795)雍和宮改建為皇家的藏傳佛教寺院,雍和宮有數量不少的泥塑佛像和巨大的木雕佛像,同時清宮中還大量鑄造藏傳佛教金銅佛像。乾隆時期的佛像許多鑄有建造年代,成為鑑別清代藏傳佛教造像的標準。
2.拉薩多覺邊肯琍瑪佛像(’dod ‘byor dpal kang li ma):
多覺邊肯是位於布達拉宮山腳下的鑄造場,始自五世達賴喇嘛阿旺羅桑嘉措(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到一九五○年代,所有為噶廈政府製作的佛像或專為噶廈政府送禮而製作的佛像,都在此鑄造,故該場鑄造的佛像非常多。
3.札什倫布寺(bkra shis lhun po)琍瑪佛像:
由日喀則札什倫布寺的工場鑄造,知名度也很高。歷輩班禪大師進貢的佛像,多屬這一類。
4.德格琍瑪佛像:主要是在四川德格的八邦寺(dpal spungs dgon pa)鑄造,為康區金銅佛像代表。由於接近漢地,極多德格琍瑪佛像流入到漢地民間。
依歷史上藏傳佛教的藝僧們的說法,造佛像本身就是佛法修持和積聚功德的事業。藏傳佛教的金銅造像雖然數量眾多,存世的精品遠多於其他地區,但由於長期以來供奉於寺院殿堂和秘藏私人的櫥櫃之中,一般人對其了解不多。近年來隨著藏傳佛教的活躍,其藝術珍品的形象才逐漸出現在一些報刊和畫冊之中。
四、東北亞
(一)朝鮮半島
朝鮮半島自古與中國關係密切。在《管子》、《史記》記載,殷商(約前16世紀~前11世紀)末年,紂王無道,箕子避往「朝鮮」,其後周武王(1134~1116 BCE在位)封其為朝鮮侯的記載。西元前三、四世紀,戰國時代的燕國人已將中國製鐵技術與漢字文化帶進朝鮮,著名的就是漢武帝(141~87 BCE在位)於元封三年(108 BCE)滅衛氏朝鮮,置四郡。三世紀時,朝鮮半島南半部的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三個部落開始兼併,至五世紀形成獨立的三國:高句麗(37 BCE~668)、百濟(18 BCE~663)、新羅(57 BCE~935),即朝鮮的三國時期(57 BCE~668),以高句麗最為強盛。
三國獨立之後,彼此爭戰不已。四七五年百濟被高句麗攻占漢山。五五一年新羅占領漢江上游,五五三年襲取百濟漢江下游,在爭戰危急中,新羅向唐朝求援,於六六○年滅百濟,六六八年滅高句麗,至此大同江以北為唐軍管轄,以南為新羅所有,史稱「統一新羅時期(668~935)」。但九○○年天下再度紛亂,形成「後三國(892~936)」分立局面。九一八年,弓裔部將王建殺弓裔自立為王,國號高麗(918~1392),九三五年滅新羅,九三六年滅百濟,半島南部又復歸統一。
在朝鮮歷史上,王氏高麗達於頂峰,仿唐制,十世紀末乘渤海灣衰落之際,勢力延伸到鴨綠江下游南岸,且與遼金爭戰。直到一二五八年被蒙古元朝(1206~1271)征服後,王權衰落。元朝滅亡後,一三九二年大將李成桂廢高麗恭讓王(1389~1392在位)自立,高麗國滅。李成桂自稱是古朝鮮後裔,國號仍為朝鮮,史稱李氏朝鮮(1392~1910),至一九一○年被日本併吞為止,前後達五一八年。
1.三國時期
一般認為,韓國佛教以三國時期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秦王苻堅派遣僧人順道,贈以佛像、經文,為其開啟接納佛教,古新羅則遲至五二八年才認可佛教的傳播。小獸林王四年僧阿道來,五年建創肖門寺以置順道,又建伊弗蘭寺置阿道,此為海東佛法之始。
高句麗時期中國遣贈佛像不多,金銅像有之,石像極少,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九六三年新羅慶尚南道宜寧郡出土的延嘉七年(539)銘佛立像(韓國國寶第119號)。金銅佛背光後有確切年代銘文,極為珍貴。這尊佛像非當地出土的作品,此正說明了佛教初傳時,高句麗居於主導地位,再由此傳至其他兩國。整體看來,實屬中國北魏、東魏(534~550)造像之風。不過前傾的舟形背光布滿火焰形雲紋,卻是中國南北朝罕見的。台座與佛身一體鑄造,相當殊異。
一九三○年於黃海道谷山郡花村面蓬山里出土高句麗五七一年造的金銅辛卯銘三尊佛(韓國國寶第85號),是最早出現的阿彌陀佛像,說明三國時期已有彌陀信仰。然而,造型上大而規整的舟形背光,常見於中國北魏河南地區;「U」形且左右相稱的衣褶紋飾,皆可見於東魏造像中。三國時期的高句麗曾出土著名的金銅彌勒半跏思惟像。
相對於北朝造像的高句麗,當時的百濟扶餘地區,不僅有來自高句麗的北朝造像系統,又因鄰近於山東半島,受到南朝佛教文化的影響極大,例如一九三六年於軍守里出土的六世紀左右石造佛坐像(韓國寶物第329號),通肩大衣,厚實柔暢手法,其下有懸裳座般的誇張衣裾,左右對稱的裝飾表現,再加上豐腴的面相,閉闔的雙眼,微翹的嘴角,露出慈祥的笑容等,在在顯現百濟佛像的典型特徵。
六世紀末百濟瑞山磨崖三尊佛像(韓國國寶第84號),矗立於忠清南道瑞山上,是百濟三大磨崖佛之一。中央主尊釋迦牟尼佛立像,衣紋極為簡練,整體渾樸厚實;面相方圓,寬額豐頤,眉眼長大,鼻潤唇厚,流露慈祥敦厚神情。其脇侍菩薩,一為持寶珠的觀音菩薩,一為半跏思惟菩薩。此類組合罕見又新穎。
一九○七年忠清南道扶餘郡窺巖面出土的七世紀金銅觀音菩薩立像(韓國國寶第293號),頭戴寶冠,披帔帛,立於蓮台上。整體修長的身軀,輕巧的曲線,尤其微微前凸的腹部、輕盈的雙手,右手上舉拈珠,左手垂下捏帛帶,令人想起中國隋代特有的佛像風味。
2.統一新羅時期
正如前述,在七世紀中葉的三國爭戰中,新羅與唐朝結盟,於六六八年合併伽耶諸國,征服百濟、高句麗,建立了朝鮮半島上首次出現的統一國家,定都慶州,前後歷經五十代國主,開創出長達二百六十七年的佛教黃金盛世。因長期與唐朝的友好朝貢關係,且與大唐盛世的佛教文化不斷交流,慶州學僧至洛陽、長安留學,不絕於途,故其造像風格自然汲取了唐代式樣的風韻。簡言之,唐代造像的雍容華貴,氣宇軒昂,量體碩大且敦實厚重的特色,完全顯露於統一新羅時期的雕刻造像中。
一九七五年於慶州市雁鴨池出土的七世紀後半的金銅佛三尊坐像就是典型的唐代風味。碩大體軀的主尊佛坐像,厚重結實,而柔暢秀致的衣紋,如流水般滑過,有輕盈明快之感。左右二菩薩的三屈式姿態,是盛唐的造像語彙,尤其輔以脫蠟法鑄造的金銅頭光透雕手法,正是隋代常見的。不過主尊像與同時期的日本法隆寺金堂第6號壁阿彌陀淨土圖的圖像頗有類似,故稱阿彌陀三尊像。
慶州甘山寺遺址統一新羅時期的石造阿彌陀佛立像(韓國國寶第82號),為聖德王十八年(719)金志誠為亡父母發願供養,是一件極度吸收唐代式樣後,又走出自身式樣的典型傑作。其身形具北周和唐代的體勢,全身衣紋處理可見笈多王朝秣菟羅式樣與手法,只是身材較短些,充滿冥想的神情;大頭寬肩,強調身軀的衣紋,以及單純簡潔的佛身造型,已走出自身新羅的特色與方向。
傳忠清南道瑞山郡普願寺發掘的鐵造佛坐像,健壯明朗、厚重樸實的體軀,圓潤的結構,穩重敦厚的體勢,顯露出大唐造像鼎盛的風華。
統一新羅時期造像代表,即慶尚北道吐含山近山頂處,建於八世紀中葉的石窟庵(韓國國寶第24號)。據傳,此座窟寺是新羅統一三國之後,景德王時期(742~764在位)宰相金大城為追念父母之恩澤而開鑿。其主尊石造佛坐像及菩薩像,整體造型、顏面、五官、神情及軀體造像手法,幾乎近於唐代天龍山,甚具西安寶慶寺大唐風味。菩薩豐滿健碩又柔暢修長的體軀,幾乎是初唐、盛唐龍門石窟的翻版。然而兩者相比,石窟庵的空間匠心獨到設計,使得每一尊造像都能從外在形式走向內在本質之美的表現。就像體的內涵而言,比唐代更加深入,尤其整體顯現出自然與抽象的結合,使統一新羅時期雕刻達到完美的頂峰。石窟庵的造像,不僅是新羅,亦是韓國造像雕刻史的分水嶺。自此之後,似乎再也見不到如此經典之作了。此座極其精密的幾何造型與高超水準的雕刻建築,一九九五年列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
3.高麗時期
高麗時期歷代諸王極盡護法之力,如太祖(918~943在位)即位後建叢林、設禪院、造佛修塔,當時寺廟幾至三千五百餘所。光宗(950~975在位)時,禪宗、天台、華嚴、唯識等宗派教團盛行,且尊崇高僧為國師,故名僧輩出,佛教鼎盛。不過禪宗講究現世頓悟修行,不重佛像膜拜,因此整體觀之,造像雖盛,然已不如其前。相對於宋代興盛的禪宗,高麗時期禪風亦大興,故藝術的製作漸漸以繪畫為主流。不過,在雕刻上,大型的鐵佛、石佛,甚而磨崖造像亦不少。忠清北道報恩郡的十一世紀法住寺磨崖佛倚坐像(韓國寶物第216號)就是典型範例。此像位於該寺捌相殿西側的巨大岩壁上,雖以淺浮雕為之,然刀法純熟銳利,帶有繪畫性,且瀟灑明朗,整體強勁厚實,落落健碩,尤其寬大的方圓面相,以及簡潔五官所表現的冥思之態,是高麗前期風格的代表作。
至於石佛,最著名的就是光宗十九年(968),由高僧慧明率百餘工匠於忠清南道論山,於穆宗九年(1006)完成,高18.12公尺的灌燭寺彌勒菩薩像(韓國寶物第218號)。整體觀之,已是極度形式化,僵硬平直,幾無造型之美,亦可見及當時地方特有的風格與觀點。其頭部達至上方的二層寶冠,幾占全身三分之一,堪稱是韓國境內最大石佛。
今藏於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的其中一件十四世紀金銅觀音菩薩像,其嫻淑的坐姿,具中國宋代風味,尤其寶冠及身軀上的繁複精緻飾物,亦可見於宋代的菩薩像上,其優雅的體軀與悠閑靜謐的氛圍,正是宋代造像的美學品味。
(二)日本
日本的佛教大約在六世紀上半葉左右,經由韓國百濟傳入,之後才開始與中國展開密切的交流,終而創造了日本獨特的佛教文化與藝術。
日本佛教的推展,最為重要的就是飛鳥時代(538~645)推古天皇(592~628在位)及其姪子聖德太子。聖德太子於推古天皇元年(593)攝政開始,即於今大阪之地建立了日本首座寺院──四天王寺;推古十三至十七年完成飛鳥寺釋迦牟尼佛坐像,即所謂的飛鳥大佛;推古十五年完成法隆寺,使佛教達於頂峰,直至六四五年左右的大化革新為止,史稱飛鳥時代,即為日本的初期佛教及其藝術的開展時期。
以即位飛鳥淨御原宮的天武天皇(673~686在位)和遷都藤原京的持統女帝(686~697在位)時代為中心,整備律令制國家,直至和銅三年(710)遷都平城為止,史稱白鳳時代(645~710)。不過,白鳳的前半期(約645~670)仍持續著飛鳥時代的美術,而後半期則是奈良時代(710~794)美術的萌芽期,故有稱奈良前期,不稱白鳳時代。此時期的日本,積極向中國學習,在政治、宗教上開始以「法」來支配與統治,使本來在中國文獻所稱的「倭」,因已為統一獨立的國家,故始稱「日本」。此時的大和朝廷持續導入以佛教為主體的中國文化,且由飛鳥和畿內周邊的豪族所支配。古墳文化(約4~6世紀)以來,自朝鮮半島移居日本的技術集團相當活躍,且七世紀時,朝鮮從三國鼎立到新羅統一期間的動盪不安,帶來新式樣的移民者,亦擔當佛教美術的各面分野。此時古墳時代的後期到終末期正重疊著,故為古墳文化與佛教文化並立的時代。
1.飛鳥時代
飛鳥時代的佛教美術是經由朝鮮傳來的中國南北朝式樣,白鳳時代則傳自隋、初唐式樣,故佛像從表現古拙美,急速進展到落落大方的古典美式樣。六世紀上半葉,藉由百濟等移居日本帶來的佛像,開始有了佛像製作。以推古期的飛鳥雕刻為中心的佛像,即所謂的「推古佛」。推古佛有二個系統,一是推定為主流的中國北朝系,即北魏、東魏、西魏(535~556)嚴格的止利派作風;另一是南朝系,略帶有柔暢作風的雕刻。前者的止利派有飛鳥大佛、法隆寺釋迦三尊像、夢殿觀音等;而後者則有百濟觀音。不過,朝鮮三國時期的佛像因不斷研究進展,令人對當時傳播樣式漸漸地清楚是以銅像和木雕為主。銅像以金銅佛占大多數,且有部分是「押出佛」(錘鍱像),木雕則是大部分由整材樟木的「一木造」像,廣隆寺寶冠彌勒菩薩半跏像為赤松木,中宮寺彌勒菩薩半跏像則是以幾塊木頭接合的「寄木造」。
此時代的佛像幾乎都著重「正面觀照」,其中亦有造像的背面僅作簡略地處理,特別是止利派造像的衣紋大多是左右相稱,面相修長,眼為杏仁形,嘴唇則呈現所謂的「古拙微笑」。尊像的種類不多,一般以釋迦牟尼佛最多,此外尚有彌勒、觀音、四天王、太子誕生像、摩耶夫人等。再者,從事造佛的匠師,為中國和朝鮮來的移民者和其子孫,其中以鞍作止利、山口大口費等最為著名。
2.白鳳時代
白鳳時代的前半期欠缺基準範例,而觀心寺的金銅菩薩立像和四十八尊佛中的幾尊,可推定是此時期製作的。若與飛鳥時代相比,造像的體軀稍稍上揚,胸部較挺,軀體微窄,腰部則粗。再者,戴有三面頭飾,身軀上有繁複的瓔珞,這樣的特色,表示在七世紀中葉帶來了中國北齊、北周的新式樣。天智天皇(661~671在位)時期,百濟、高句麗相繼滅亡,擁有高度新技術而歸化日本的移民者中,就有像國骨富的人才,再加上此時乾漆像、塑像、磚佛等的新技法。天智天皇五年(666)野中寺的思惟菩薩半跏像的衣裳邊緣就可見到自波斯帶進的隋朝聯珠紋。天武天皇十三年(685)敕令每一家造佛寺,並安置經典,因而造成此時代有極多的小金銅佛像,而其造像具有厚實量感,且又典雅柔暢,就是受到隋、唐的影響,興論寺佛頭和當麻寺彌勒佛坐像,就是一個明顯的作例。直到持統朝(686~697),藥師寺金堂藥師佛及脇侍像三尊像的圓熟體軀,以及日光、月光二脇侍菩薩柔暢姿形,自由衣紋的表現,正是初唐式樣的特色。
3.奈良時代
自和銅三年遷都平城京(今奈良)至延曆十三年(794)遷都平安京(今京都)止,史稱奈良時代。然其中心在天平年間(729~749),因此在美術史上稱天平時代。亦有視此時代為前代白鳳時代的後半,故稱其為奈良前期。此時期大力整備律令法制,仿傚唐代長安城,積極建設平城京,在中央集權的體制下,佛教昌榮,遷移到新都的佛寺,不僅祈願鎮護國土,而且綻開燦爛的佛教文化芬芳。聖武天皇(724~749在位)發詔全國建立國分寺,於東大寺造立大佛像。再者,承續前代派遣唐使,透過盛唐文化,帶來印度、波斯等西方美術,因此在奈良的寺院和正倉院可見到堂皇的造型與華麗的裝飾技術。不過,聖武後期因發生瘟疫與律令法制的動搖,政治逐漸不安,此時官營的建寺、造佛已全面形式化。天平勝寶六年(754)以來,從鑑真為主的唐招提寺相關的建寺、造佛正可以見到持續到下一時代的式樣。
在佛像的雕刻上,不僅吸取唐代式樣而開展,而且視為國家事業,造佛之風大行,於是佛像的式樣、技術亦漸臻嫻熟,完成了所謂的古典雕刻。此時又流行寫實卻優雅明朗的作風,體軀均勻整齊,面相已脫稚氣,走向圓熟知性,甚有表現出深刻苦惱的表情,再者,天部像已出現自由活動的姿形和體態。此時代的前半期,有造東大寺司等的造佛所,許多活潑的匠師們,以東大寺盧舍那佛(奈良大佛)為首,製作了東大寺法華堂諸尊像等巨像。其中,指導東大寺奈良大佛營造的國中連公麻呂、製作興福寺十大弟子及八部眾像的將軍萬福、製作石山寺的志斐連公麻呂和己智帶成等佛師,皆是歸化人系。技法上,以適於塑形的表現,即金銅像、乾漆(夾紵)像、塑像為主流,而乾漆像,前半期的遺品大多為脫乾漆造,後期則以木心乾漆造為主。此時,亦盛行磚佛、押出佛、石佛的製作,技法種類之多,是前所未見的。
金銅佛有東大寺藏太子誕生像;脫乾漆像有東大寺法華堂不空●(上四+下絹)索觀音菩薩像、興福寺十大弟子及八部眾像、唐招提寺盧舍那佛坐像;木心乾漆像有聖林寺十一面觀音菩薩像;塑像有東大寺戒壇院四天王像、新藥師寺十二神將。營造奈良大佛以後,引起財政困難;佛像大量生產,使得官營造佛所的製作,有明顯的類型化傾向,天平後半期起民間的造佛所和僧侶們製作的木雕佛像,反而令人感到有生命力,如八世紀末神護寺的藥師佛立像、唐招提寺的木雕群像等,持續到平安時代(794~1185)前期的雕刻風格。
4.平安時代
自延曆十三年遷都平安京到平氏滅亡的文治元年(1185),大約四世紀間,即史稱的平安時代。寬平六年(894)停止遣唐使之時,即為平安前期,或稱弘仁(810~824)、貞觀(859~877)時期,其後則為平安後期,或稱藤原時代(894~1185)。平安前期致力於奈良時代以來的唐風文化,是走向國風文化的過渡期。當時朝廷雖禁止平城京諸大寺遷移至平安京,歡迎入唐求法的最澄、空海新開創的天台宗、真言宗。最澄在比叡山延曆寺,空海在高野山金剛峰寺、東寺(教王護國寺),以密教咒術祈願鎮護國家,也影響到地方,即所謂的密教美術。神道與密教的交流中,開啟本地垂跡說,即垂跡美術。宮廷中盛行漢文,書法水準提升,九世紀下半葉出現了「假名文字」。
九世紀末以大唐為中心的亞洲文化圈崩垮,日本亦在平安後期斷絕與唐代的來往,促使國風文化延伸成長。十世紀左右起,莊園集中於權貴,孕育出藤原氏攝關家族勢力支撐而起的華麗王朝文化。敕撰《古今和歌集》以來,興盛和歌對優美的「假名」書法、四季和自然表現的纖細感情,促使了「大和繪」的展開,在各個領域上成立了和樣,成為後古典的日本文化。十一世紀上半葉藤原道長、藤原賴通的時代,為王朝文化的完成期,亦為末法思想的展開期,壯麗地表現出阿彌陀淨土的思想。
十一世紀末開啟的白河、鳥羽、後白河上皇的院政,因「受領層」(即地方官)經濟力的發展與支持,盛行建寺造佛和熊野御幸,表現了更為洗練、耽美傾向的王朝美術。取得政權的武士團平氏,因沉溺於王朝文化而被滅絕,但卻出現了關心庶民的說話文字和繪卷物。這時因與宋代文化接觸,開始出現新的徵兆,走向中世的轉換期。
奈良時代末成立的造東大寺司和造法華寺司,雖平安時代已被廢,這些官營造佛所的工匠,並未全部轉職,在九世紀上半葉尚有被推定為佛教造像者,於部分的木雕中就有使用乾漆補助潤飾的雕像,例如教王護國寺講堂諸尊像、廣隆寺講堂阿彌陀佛坐像、神護寺五大虛空藏菩薩像、觀心寺如意輪觀音菩薩像等。這類佛像大多為朝廷和空海弟子以及真言宗系脈的僧侶發願而造。另一方面,八世紀開展的民間佛師系統,亦積極地製作木雕像。或以「一木造」不施色彩的素木雕,有神護寺的藥師佛立像、新藥師寺的藥師佛坐像;或以銳利的刀法,表面上再施以彩色的,有元興寺藥師佛立像,向源寺十一面觀音像;檀像的有室生寺彌勒菩薩立像、法華寺十一面觀音像等,這些像皆優雅,且有量感,雖表情嚴肅,卻帶有神祕的情愫。
九世紀下半葉,佛像量感漸減,面相又再呈秀雅,乾漆系雕刻上出現木雕翻波式衣紋;木雕像的螺髮,使用乾漆。這二種系統,在式樣與技術上的融合,形成了藤原時代的和樣雕刻。此時期居於本地垂跡說製作的佛像雕刻,著名的有教王護國寺和藥師寺的僧形八幡和二女神像。隨著佛教向地方傳播,製作了黑石寺藥師佛像、勝常寺藥師佛三尊像等。十世紀的造像,約於延長二年(924)法性寺千手觀音菩薩像、天慶九年(946)岩船寺阿彌陀佛坐像等,出現了和樣的傾向,即圓潤的顏面加上親切的表情,肩線平穩順暢,衣紋則取以淺雕;寬弘三年(1006)康尚所作的東福寺同聚院不動明王像、長和元年(1012)康尚派所作的廣隆寺千手觀音菩薩像上,極為顯著。
另一方面,在奈良活躍的佛師作品,如興福寺藥師佛坐像,出現強韌明快的身軀調和的感覺,令人感到天平的復古。活躍於藤原時代後半期的定朝,對其師康尚的作風和奈良系的傳統做了統合,屏除木雕的要素,回到塑形的表現,天喜元年(1053)平等院鳳凰堂阿彌陀佛坐像,即為其代表作。圓滿調和的佛像姿形,極度適合末法不安人心的淨土觀想。飛天背光和多重蓮花座等的莊嚴具,開創了華麗的式樣,完成「寄木造」的技法。定朝組織了大規模造佛所,成為擔當僧綱位的首位佛師,使得定朝式樣成為雕刻界的主流,達一世紀之久,地方亦甚為普及。其後造佛所分立,在興福寺者,稱為奈良佛師,在京都者,則從事於與貴族有關的造佛。定朝的後繼者亦極有勢力,廣隆寺的日光、月光菩薩像和十二神將像等,亦表現出優美的作風。再者,法界寺阿彌陀佛坐像和淨瑠璃寺的九體阿彌陀佛坐像等,皆忠實沿襲著定朝式樣。到了十一世紀末,造佛成為往生極樂的重要功德項目,由於大量的生產,促使作風上、形式上皆走向僵硬化。十三世紀中葉左右,因奈良佛師嘗試自由創作,嵌入玉石,終誕生出仁平元年(1151)長岳寺阿彌陀佛三尊像等,表現堅強意志力的鎌倉雕刻萌芽。再者,此時代亦誕生鉈雕和「五木佛」的特殊地方式樣。在臼杵磨崖佛像和大谷寺石窟等,出現相當大規模的磨崖石佛雕刻。
五、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與印度南端僅一海之隔,印度的佛教文化自阿育王時代起就相繼傳遞過來。諸多傳說,雖都有記載佛陀曾蒞臨此地三次,然實止於傳說。一般而言,阿育王派遣其子及女兒,即摩哂陀、僧伽蜜多至此地傳法,應是開啟斯里蘭卡佛教之始。
斯里蘭卡的佛教及其美術,可從三個古都來探索,即阿努拉德普勒(Anuradhapura)、波羅那魯瓦(Polonnaruwa)、坎底(Kandy)。而一二九三年南印度塔米爾人來犯,迫彼再度遷都,其後五百年幾乎是佛教的衰微期。
三世紀時大乘佛教便傳入斯里蘭卡,然因上座部的阻撓,發展並不順暢,直到八、九世紀才開展起來。不過在造像上,四世紀時便傳來南印度阿瑪拉瓦提風格的式樣。像奧卡那大佛(Aukana Buddha),就帶有龍樹丘的佛像特色,直立規整,高大厚重敦實的軀體,飾以整齊有致且又柔細衣紋的式樣是當時主流。那堅實量感的厚重頭部,直視前方的模樣,在在道出阿瑪拉瓦提的龍樹丘造型風味。印度波羅王朝(Pala,約8~12世紀)的美術風格亦傳入斯里蘭卡,如觀音菩薩立像及多羅菩薩像,皆可見波羅美術的風味。
六、尼泊爾
大約200平方公里的加德滿都谷地,寺院、佛塔,以及為數眾多的雕像星羅棋布。據當地傳說,早在阿育王在位時,這裡就有了佛寺,無論這個傳說有多少的成分屬實,但千百年來,這裡確實一直崇信著佛教、印度教。而且這裡自古以銅聞名,印度古代文獻就曾提及尼泊爾出產高品質的銅,尼泊爾的古代銘文也記載其金屬製品輸出印度之事。七世紀中葉,唐朝使節王玄策往訪印度時取道尼泊爾,就對尼泊爾的金工製品留下深刻印象,但早期遺留的金工製品很少。
尼泊爾現存最古老的雕像群,明顯透露出笈多(鹿野苑)的痕跡,其年代大約起自六、七世紀。之所以如此,可能與下列因素有關,尼泊爾與印度相鄰,從加德滿都谷地穿越山脈可達印度;雙方一直有來有往;笈多王朝時有位尼泊爾首領是笈多君王的封臣(類似諸侯),尤其笈多是印度藝文史上極為興盛的年代,中心的藝術風格易於向地方擴散,一尊帶著五九一年題記的佛像就是一例,佛跣足立於蓮台上,薄如蟬翼的僧衣彷彿在微風吹拂下輕揚;螺髮顆粒細小,半開半闔的眼睛如同含苞待放的蓮花;鼻梁直挺,下唇較為豐厚,五官及整個面部表情散發出清朗、祥和、輕安的定靜三昧。另一尊大約七世紀的佛立像,肉髻比上述的佛像微尖,這種造型,為後代許多雕像提供了模型。雖然帶有笈多風味,但這些雕像卻呈現強健有力之感,可能是受了秣菟羅風格的影響所致。
九至十二世紀間,印度與西藏之間如同過去幾百年持續進行著經濟文化交流。尼泊爾在地理上介於北印度、西藏之間,向來是兩地間交通的管道、貿易的樞紐之一。藉此之便,尼泊爾當地以及來自印度、西藏的學者及學生們,在此傳道授業,研習義理,討論宗教和文化藝術,並且篤行實踐。
十二世紀前後,印度佛教衰亡,縱使源自印度的佛教及其藝術之「泉」止息了,但尼泊爾崇奉佛教,也繼續造像,成為延續佛教法脈的支脈之一。不僅如此,尼泊爾也成為西藏僧侶在印度佛教滅亡時,轉而尋找佛教藝術靈感的新泉源。
雖然早期深受印度影響,但此時尼泊爾自身的樣式逐漸形成,並嶄露頭角,終至燦然可觀。一方面是因為來自印度的泉源枯竭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在長久的薰習下,對雕像製作已然嫻熟。這時雕像的身材大多苗條,看來亭亭玉立,儀態秀美,線條流暢婉約。舉例如次:一尊文殊童真像,身形圓渾,雖然雙腿的比例略小,但整體可愛自然,身材形貌都好像真的孩童一樣。又,很多佛像結禪定或觸地印,安詳地靜坐沉思,頭後有頭光,用以表徵其神聖;頭形勻稱,頭上肉髻滿布螺髮;眼睛半開,雙唇豐厚,耳垂長,神情清朗。薄薄的僧衣一角繞過胸前,覆蓋在肩上,身體看來健康年輕,簡約、自然、高雅。
這時,有些新的趨勢出現。首先,在裝飾上愈來愈繁複,細部更是受到關注,無論何種材質的雕像均如此,尤其十世紀後。其次,在製作多臂造像上,技術愈見純熟。眾多手臂都能從雕像的肩膀兩側自然伸出,不會突兀。再其次,過去蓮座上下兩層的花瓣常常相互交錯,但此時上下兩層的每一瓣都相互對準。又,精美的木雕像出現,在許多上乘作品可在尼泊爾各寺院的支柱上找到。有的雕像位在柱子上;有的雕像本身,就是用以支撐殿堂的柱子。另外也有獨立圓雕的木質造像。
十三至十五世紀,可說是尼泊爾雕像的黃金時期。許多雕像既非黃銅,也不是青銅所鑄,而是銅,並且鍍了水銀。其次,菩薩像寬肩細腰,比例勻稱,多數採三屈立姿,看來身軀曼妙,優雅美觀;裙褶下襬呈燕尾狀,具有動感。雕像上鑲嵌了真正的珠寶,依照天然的形狀磨圓,不加砌面,因此整座雕像流露出一種高雅華麗、精緻圓潤的美感。由雕像(主要在腹部、裙褶上)細細密密分布的裝飾紋樣可知,工匠確實灌注了無數心血。上述特質,使尼泊爾的雕像在幾百年後的今日依然散發魅力,引人注目。
尼泊爾的雕刻造詣日高,名聲遠播。工匠精湛的技藝、精良的成品,贏得「喜馬拉雅山地區最佳作品」的聲譽,工匠也得以常常獲邀到各地。例如,阿尼哥曾被迎請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宮廷內府去製作雕像,也曾應邀到鄰近的西藏去傳授經驗。自十五世紀末至十八世紀中葉,密教人物像(尤以多臂的)頗為流行,佛陀造像消失大半。當時的造像依然華麗,某些造像的身軀較之前的誇張些;忿怒像、雙身像的數量與日俱增。越到晚期,越強調細部,趨於繁複,例如背光、寶冠、衣飾、台座等,佛陀胸腹之間的衣物,裝飾得如同工筆刺繡或緙絲一樣。相對的,雕像內在的精神底蘊,似有受到忽略之勢。
七、東南亞
在東南亞區域裡,佛教主要是流布於緬甸、柬埔寨、泰國、寮國、越南(亦即大陸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以上屬海島東南亞)也曾流行佛教,但在十四世紀前後逐漸轉信伊斯蘭教。由於東南亞主要流行南傳上座部佛教,在佛教藝術上受其啟發之處頗多。在人物上,多為教主釋迦牟尼佛及其弟子。在題材上,多與佛傳、本生故事、弟子、護法善信等有關。在風格上,受印度及周邊地區影響,東南亞各國彼此間相濡以沫,並有自己的創造發明;近代西風東漸,東南亞佛教雕像也出現西洋的痕跡。在材質上,現存者以金屬、石質的居多,因為這些比木、竹、土、革更能抵抗東南亞濕熱的氣候。從流傳至今的作品可知,東南亞各國的佛教雕像同中有異,各有千秋。
(一)緬甸
早期(3~9世紀)留下的雕像為數雖少但已然可觀。雕像出自幾個地方:直通(Thaton)、庇古(Pegu,今勃固Bago),以上均為孟人(Mon)群居之處;驃(Pyu),在緬甸中部;阿拉坎(Arakan,今若開Rakhine),近孟加拉灣。可能因為緊鄰印度且印度佛教藝術高度發展的緣故,因此這些雕像的印度風味頗濃(尤其是笈多)。以驃國雕像為例,佛陀常結跏趺坐,施觸地印(又稱降魔印),這種姿勢及手印,為日後緬甸的佛像立下典範。又,驃國遺址曾出土金箔、石碑,上有巴利文銘文。由於當時不同部派並存,因此除了釋迦牟尼佛像之外,也有觀世音菩薩像等。
九至十三世紀的雕像,主要是南傳佛教體系。十一世紀蒲甘王朝(Bagan,約849〜1287)的阿奴律陀(Anawrahta)一統緬甸,奉南傳佛教為國教,因此雕像的主要人物是佛陀釋迦牟尼。蒲甘王朝是緬甸佛教藝術史上的黃金時期,雕像馳名遠近。佛像肉髻通常不大,頂上常有小而尖的火焰形佛光;雙眼常微張俯視,眼瞼線條呈波浪狀,從鼻根、雙眉之間向兩側的太陽穴延伸;其鼻子挺直略長,下巴略尖,嘴角含笑。佛坐像衣服貼體薄如蟬翼,右肩偏袒,左肩上常有僧衣一角;右手多作觸地印;佛立像的僧袍自雙肩到小腿,呈對稱垂下。阿難陀塔寺(Ananda Temple)中心柱的四尊立像頗具代表性。其南、北向的,各作轉法輪印;佛立像作轉法輪印的,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少見。其次,某些十二、十三世紀初的佛像狀若沉思,帶著淺淺的微笑,可能有來自高棉吳哥的影響。
蒲甘王朝被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在位)的大軍滅後,緬甸進入多國林立時代,後來雖再度統一,但穩定性不足,各地的佛像仍各具特色。例如,庇古佛像的頭光形狀常如拉長的蓮苞;頭部、寶冠及佛光幾乎占雕像高度的一半。阿瓦王朝(Ava,1364~1555/1752)有些佛像貌如孩童(因佛陀純潔一如孩童);十五至十七世紀期間流行無量壽佛、藥師佛像。約十七世紀起常見一種寶冠佛,雙耳垂肩,戴著及胸(或臂膀)的珠玉環璫;寶冠兩側延伸出來的飾物如展翅的鳳蝶一樣,對稱均衡,精緻莊嚴,尤其是阿拉坎、撣邦(Shan)的。貢榜王朝(Konbaung,1752~1885)仍流行右手作觸地印的佛坐像,但佛立像也不少;有時可見佛右手拈著藥果,象徵佛陀是身心性靈上的大醫王。王朝末期以曼德勒(Mandalay)為都時,佛像看起來年輕,常有自然的笑容,衣裝大多華麗細緻並飾以許多小玻璃、小鏡片,或上漆、鍍金(據信佛陀膚色如金銅)。
另外,緬甸雕像還有幾個特點:一、本生故事的雕刻最遲在五世紀就已出現,常見於塔寺壁上。本生故事不但是緬甸佛教藝術常用的題材之一,也是千百年來緬甸文學、樂舞、表演藝術取之無盡的泉源。二、那特(Nat)是重要的在地信仰。其崇拜對象包括古聖先賢、神話人物、自然界精靈等。那特雕像常常躋身於佛弟子或護法之列。三、緬甸森林蓊鬱,柚木多,木雕佛像品質頗佳。
(二)柬埔寨
前吳哥(pre-Angkor,802之前)的雕像頗具特色。例如,頭上常有馬蹄形的拱(從足部連到手、頭、背後),以支撐厚重的雕像。造像筆直挺立,並無三屈立姿的模樣。但身軀各個部位,如鎖骨、手肘、腕、膝蓋等比例,都留意到了;連嘴角上的鬍鬚也一刀一刀刻劃出來。此外,肌膚表面從上到下都打磨得光滑整潔。衣服的皺褶大多以淺線陰刻表現,偶有陽刻。衣服下的軀體明顯可見,絲毫不受衣飾紋樣的影響。
八○二年,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802~850在位)於神廟加冕,除宣示嶄新時代的來臨,更強調自己與神明間產生強大的連結。這驚天一舉,也開創了雕像的新氣象。例如,馬蹄形的拱幾乎都消失了,雕像獨自站立,原本用以支撐的憑藉改以厚重的雙腿取代。於是,雕像顯得更為強健有力,相對地也減少了一些優雅。這時菩薩(如觀音)的造像不多,但神情上輕鬆自然,清新又有生氣,混合著笈多、後笈多、高棉在地的風格。
從九世紀末至十一世紀末(遷都吳哥地區開始),出現了部分極精湛的作品。吳哥初期的雕像略顯平板,臉龐大,肩膀寬直,軀體四肢頗為厚重。自然彎曲的眉脊,現在幾乎呈水平的一條線,五官刻劃清楚。若頭戴寶冠,則寶冠有精細雕刻的珠玉;若無寶冠,則顯露出各種美麗的髮型。女王宮(Banteay Srei)的門楣上有裝飾性、敘事性的浮雕;雖面積不大,但繁複有序的構圖、精緻細膩的雕工,營造出珠圓玉潤般的美感。
上述風格,進一步發展為巴方樣式(Baphuon),其雕像之美,可以從頭髮、衣裝、結飾等方面來觀察。頭髮上,穗狀小辮子一束束地刻寫清晰,其間交織著精美珠玉。眼睛鑲嵌寶石,嘴唇則以細線刻劃。腰際如蕾絲般的紋路,描摹細膩。干縵(亦即下裳,又稱橫幅)緊密貼體,其上整潔有序的皺褶及結飾,了了分明。結飾都是慧心設計、巧手製作,類似蝴蝶翼的模樣。仕女的下襬裙角則為各式魚尾的造型。雖然雙肩依然寬闊,但身材勻稱;男性顯得健康,女性看來修長。不論男女,頭顱輪廓、頭髮造型均呈圓弧形;臉頰圓潤,臉上帶著酒窩,下巴中間有一條細線。整體來說,此時期的雕像,流露出青春的生意,散發出甜美文雅的氣質。
吳哥時期(約9~15世紀)帝國臻於鼎盛,在雕像上也有相應的成就。男性雕像體格健壯,四肢結實。寬寬的臉龐有稍微隆起且相連的雙眉,眼珠微凸,瞳孔清楚地刻劃,雙唇厚實,讓雕像具有威嚴感。雕像腰際的衣帶(即山樸,Sampot)常摺成半圓形、錨形或魚尾狀,袒露的上半身飾有瓔珞珠玉;若頂戴寶冠,則冠上常有帶狀的裝飾紋路,如蓮葉、菱形、珍珠、幾何紋等;耳墜常呈圓錐狀,且垂到(或逼近)雙肩。這些較為柔和的元素,中和了上述的威嚴面相,讓整座雕像在嚴肅之中帶有溫和。要言之,這時期的佛像多頂戴寶冠,如君王或神明一般,而且兼有早期的粗獷、中期的文雅。
巴戎時期(Bayon,1181~約1220)的雕像自成一格。之前,多數帝王信奉印度教並自比神明;但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1181~約1220在位)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其自比的是觀音菩薩。自九世紀以來帝王雕像就是神明像,而神明像也就是帝王像;所以闍耶跋摩七世時的帝王像,經常是觀音菩薩像,而觀音菩薩像基本上就是以他的容貌為模型:中老年人相貌,額頭光潔,頭髮上梳,髮髻整潔有序;眼睛半闔,視線朝下,嘴角帶著一抹淺淺的微笑,好像低頭沉思或在傾聽民瘼般;服裝大抵素樸,猶如簡單的僧衣。
當時較為流行的是佛陀、觀音菩薩、般若佛母等。佛陀或以單尊的結跏趺坐像出現,或以龍王護佛的模樣出現。觀音立像常有四臂、八臂,且頂戴寶冠或高梳髮髻;上半身有時滿布小型禪定像,有的則除胸口、上臂、手腕有珠玉之外,一無飾物。其次,三尊像也不少,主尊之容顏常類似上述的沉思傾聽者。值得一提的是飛天(apsarasas)浮雕。飛天典出印度,在吳哥化為千姿百態的小身影,翩翩飛舞於宮垣、樓閣、庭榭中。上述多種風格形式的雕像,出現在帝國遼闊的版圖裡,東達越南中部,北到寮國南部,西至泰國中部、東北部。
十三世紀後,吳哥帝國逐漸傾頹。一四三一年吳哥京城遭泰國攻陷,帝國遷都南方,甚至被泰國納為藩屬。柬埔寨雕像也受此大勢影響;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雕像流露出泰國大城(Ayutthaya)的風格(見下文)。十七至十九世紀,國勢陵夷,許多佛像的裝飾頗為簡約,而且似乎帶著沉思、淡淡憂傷的表情。
(三)泰國
六至十三世紀間,在今天稱為泰國的這片土地上,同時存在著幾個先驅文化,如他叻瓦滴(Dvaravati)、華富里(LopBuri)、泰南室利佛逝(Srivijaya)等。
他叻瓦滴主要在今泰國中部,住民以孟人為主,這是東南亞最早信奉南傳佛教的國家之一。雕像的特徵是肉髻大,頭髮卷曲,通常沒有頭光;顏面寬大,稍微扁平;眼睛長,視線朝下,眉毛彎彎長長,雙眉在鼻根處相連。在衣著上,多穿通肩袈裟,衣帶自雙手腕部垂下,形成一個大「U」形。這時有兩種雕像頗為流行,一是龍王護佛,在泰國出現的時間,早於東南亞多數國家,其他區域並不常見;二是大型立體法輪像,法輪像的底座常有一兩隻小鹿,象徵佛陀初轉法輪。該主題在印度偶而可見,但他叻瓦滴時期(約6~13世紀)留下的法輪像之大、之多,獨步全球。
此時期一些獨特的樣式、主題:一是佛像雙手均作說法印。印度佛像只有一隻手作說法印,但他叻瓦滴時期不少雕像的兩手卻同時結說法印;二是佛陀立(或坐)在一隻奇特的動物身上。這種動物具備了印度教三位主要神明:濕婆、毗濕奴、梵天各自的坐騎特徵,也就是牛(對應濕婆)的耳朵,金翅鳥(對應毗濕奴)的嘴,鵝(對應梵天)的翅膀。由此可知,當時泰國中部已有印度教、佛教,而且造像者可能認為佛陀高於印度教神明。
另一個先驅文化是華富里,其位置主要在今泰國中部、東北部。當時華富里的佛菩薩像透露出來自吳哥京城的巴方、吳哥、巴戎等風格(請參考上一節)。因為,當時吳哥帝國蒸蒸日上,泰國中部、東北部是深受其影響的地區之一。華富里的某些雕像就穿戴著王袍、皇冠,類似吳哥帝王的模樣。其中有些雕像的容顏,可能是以闍耶跋摩七世為模型所刻,例如一尊出於披邁寺(Phimai)的佛坐像即是。有的雕像不僅穿著王服,而且上半身滿布一列列細密的佛坐像。
第三個先驅文化是泰南室利佛逝,此處曾深受室利佛逝王朝(約7~13世紀,今印尼蘇門答臘及爪哇、泰國南部、馬來半島一帶)影響,也曾是東南亞最繁忙的路口之一,商旅雲集,物資豐盛,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帶進五花八門的貨物、各式各樣的文化,因此該地接觸並吸收了多種藝術風格,例如笈多、阿瑪拉瓦提、波羅、帕拉瓦(Pallava)、朱羅(Chola)、中爪哇、高棉、占婆(Champa)等。在這個基礎上,泰南室利佛逝創造出一己的新作,這些作品大多臉頰豐滿,眼睛半開,嘴巴較小;四肢修長,偏袒右肩。菩薩像的寶冠或高髻上珠玉玲瓏,胸口、肩上、手腕、腰際都有細緻的飾物;一尊在素叻他尼府猜呀縣(Chaiya, Surat Thani)維安寺(Wat Wiang)出土的觀音像即是典型佳作。
泰國自素可泰時期(1238~1438)正式獨立建國。當時,蘭坎亨王(Ramkhamhaeng,1279~1298在位)不僅武功顯赫,在文治上也卓然有成,並對泰國的文化走向產生長遠影響。他創制泰文,並對外取經,例如向當時南傳佛教的中心──斯里蘭卡,學習佛教及其藝術,也向蘭納泰(Lanna Thai,今泰北)學習佛像製作,還承續較早的傳統,如他叻瓦滴時期的建築樣式。藉此,素可泰一步步形成自我的藝術風格。
十四世紀中葉,素可泰就有相當精美的雕像了,這些佛像頭上有火焰形佛光、隆起的肉髻、細細的螺髮,鵝卵形臉上有美人尖、彎如新月的眉毛、略鉤的鼻子、略小但上揚的雙唇、慈祥的表情、溫和的微笑;身材修長,肩膀寬,胸膛高挺,腰部細。肩膀上的衣帶垂到臍部,並且在末梢略呈鋸齒狀。整體看來和諧優美,線條流利。素可泰時期最特殊的作品,是獨立的佛行走像。佛行走的姿勢早已出現在印度的佛教藝術裡,但止於浮雕,僅是印度藝術裡的滄海之一粟;但泰國將其擷取,以獨立圓雕的形式呈現,冠以泰人的容顏、素可泰的火焰形佛光、素可泰的雕像造型,而且大量複製。於是,佛行走像成為泰國特有的雕像之一。
大城時期(1350~1767)的泰國頗稱富庶,為其文化藝術的發展提供了厚實基礎,佛教藝術界也出現許多佳作。一開始,雕像的臉孔平扁寬大,眼皮直而下垂,嘴角稍稍上揚,螺髮顆粒小,螺髮與額頭之間有一道飾帶,左肩上的衣帶尾端方正平整,這是烏通(UThong,大城的發跡地)雕像之特徵。大城也取法素可泰風格,畢竟素可泰時期的藝術造詣極佳;同時,高棉的某些元素(如方形臉、肅穆的表情)也具影響力。接著,大城一統泰國,其雕像也呈現融合各家的態勢,例如,佛坐像左肩上的衣帶尾端平整,但臉形沒有高棉的方正;佛行走像是一直延續下來的主題之一,但表情嚴肅。蓮台的裝飾極為華麗,可能與當時物阜民豐,信徒有能力出資為佛像上金有關;又因國王有神格化的傾向,與百姓較有距離,故國王雕像看起來較為嚴肅。
這時,高僧瑪萊入地府的故事漸漸流行。傳說他到地府去看受苦受難的鬼魂,牢獄慘狀極其可怖,難以描繪。他悲痛莫名,想返回人間時,漫山遍野的鬼魂一擁而上,有的摸著他的雙腳、捉住他的衣角,有的仆倒跪拜、涕泣垂淚,他們一個個捶胸頓足,滾地哀嚎,哭聲震天,託他帶口信給陽世親友「多做功德,幫助鬼魂脫離苦海;慎勿為惡,以免日後下生牢獄」。不只故事流行而已,雕像也隨之流布。造像中瑪萊站在台上;台下餓鬼有的合掌高舉,有的頂禮懇求,有的爬行號叫,他們全都枯瘦如柴。
現代泰國的佛像頗受西洋影響,在主題上則一貫是南傳佛教的。泰國在十九世紀中葉變法維新,趕上世界潮流;其改革的範圍包括藝術,但工匠仍取材於古老的經典。於是,泰國出現許多西洋寫實風格的佛像,作品具現代感,又不偏離泰國千百年來的信仰。二十甚或二十一世紀問世的龍王護佛像、佛行走像,都是很好的例證。
(四)寮國
寮國西北部與緬甸、泰北接壤,西部與泰國東北部相依,南部與柬埔寨為鄰;這些鄰國在藝術上都相對強勢,故寮國的佛像受這些鄰近國家的影響頗大。
雖然史學家多把寮國的開國年代定在十四世紀中葉,但其歷代祖先早已在當地篳路藍縷開啟山林,並且世代居住,留下多種文物。十一世紀之前的雕像,有泰國他叻瓦滴時期的特徵,例如臉龐較寬,嘴唇較厚,細細彎彎的雙眉在鼻根上相連等。十一世紀後,有些雕像透露出高棉吳哥的特徵,可能是以闍耶跋摩七世的相貌為模型的帝王雕像,這應與吳哥的擴張有關。
據傳,寮國在一三五三年獨立建國。之前,小王子法昂(Fa Ngum)與父親都沒有得到祖父的喜愛,兩人被驅逐出境,流亡柬埔寨;小王子在當地受教、成長,並與柬埔寨公主成婚。後來,小王子的岳父派兵護送其還鄉、攻入都城,即位為王。隨後北上的,還有柬埔寨的僧侶、學者、匠師等。由於新國王大量採用柬埔寨文化,因此新成立的寮國在許多層面都深受柬埔寨影響,如宗教、雕塑、樂舞等。(一四三一年,吳哥京畿被泰國攻占,都城南遷,對寮國的影響力轉弱。)
十四世紀後,寮國的雕像與蘭納泰、素可泰、大城的雷同,較為顯著的是佛行走像。雕像的身軀線條看來優美流暢,臉呈鵝卵形,鼻呈鷹鉤狀,這種造像的模型,應該源自素可泰。其次,許多佛坐像施觸地印,不少佛像頭戴寶冠,寶冠有八角,衣袍上多有金屬絲線的裝飾,這些可能是來自大城的影響。
十七、十八世紀時,寮國佛像類似蘭納泰、大城的。當時佛像服裝大致可分兩種:一種穿王袍,戴皇冠。耳後、頸項、手臂、腳踝等處,都有金銀細絲所成的華麗裝飾。之所以有君王般的服飾,原因之一是信徒敬愛佛陀,認為佛陀是最為尊貴的,因此以世間最高等的禮品(金)奉獻,供養三寶;原因之二是大城當時的君王有神格化傾向:君王就是當世的佛,也就是神明;神明下凡為君,理當穿金戴銀;另一種佛像只穿簡單樸素的僧衣,如苦行的僧侶一樣,因仍有僧侶、弟子篤信佛陀原本就割捨世間一切的榮華富貴,追求生命的智慧。十八世紀後,佛像(尤其是立像)常常就以整棵樹的樹幹所成;這些雕像看來相當高瘦,有的甚高達2公尺。
(五)越南、占婆
越南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很大。自秦漢至唐朝,越南北部都納入中國版圖,長期下來,越南受中國的影響很多,例如法政制度、學術思想、宗教及其藝術等。中國的佛教以大乘為主流,許多中國或越南僧侶在該地弘法或駐錫(如義淨就記錄了運期、木叉提婆、窺沖、慧琰、智行、大乘燈等),因此越南的佛教及其藝術也有濃厚的大乘風味。這一點,不同於東南亞大多數國家。
越南的佛菩薩像,是受中國影響甚為明顯之其中例證:一、在佛教母國印度,觀音菩薩以男性的相貌出現。觀音圖像剛剛傳抵中國時,也是男相,到唐代才開始有女性化的觀音造型;後來,觀音的容顏甚至宛如母親般,慈眉善目,和藹可親。越南的觀音造像,就與中國的觀音一樣,祥和慈悲。二、在印度,彌勒菩薩也是男身。彌勒信仰初抵中國時,在圖像上也是男相,到五代出現了心寬體胖、笑容可掬的彌勒形象,後來彌勒幾乎定型為袒胸露肚、滿腔歡喜、類似布袋和尚的模樣。越南的彌勒,也是這般的樣貌。
另外,較著名的還有阿彌陀佛、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由於大乘興盛,而且禪宗、淨土宗或禪淨雙修的思想蔚為主流,因此淨土思想的阿彌陀佛幾乎人盡皆知。彌陀像常被供奉在越南寺廟的大雄寶殿。又,由於臨終來迎的思想受到歷代祖師大德的傳揚,因此阿彌陀佛通常是立像(以示來迎);而且阿彌陀佛身旁常有觀世音、大勢至作為脇侍,亦即三尊一起出現,稱為「西方三聖」。有時彌陀也採坐姿,與藥師佛、釋迦牟尼佛等一同趺坐於大殿。另,觀音菩薩不僅出現在「西方三聖」中,還常常單獨以千手千眼的形象出現,造像頗多。
概括地說,越南佛菩薩像有些特徵:佛像肉髻低,雙目通常垂視,袍服覆蓋雙肩,中衣結帶。姿勢上,結跏趺坐時多單盤,這與不少東南亞雕像一樣。有些菩薩像戴著頭冠(未必是高梳髮髻);有些觀音頂戴五方冠,某些地藏菩薩的造型相同。無論是佛、菩薩、羅漢或弟子像,比例上常是頭稍大、身材苗條。材質上,木雕較多,金石像少。木雕上層層髹漆(越南亦精於漆器),有的再上金箔,使整個雕像散發出肅穆寧靜之感。
越南的國土上還曾存在一個國度──占婆。占婆主要位於今越南中部。從當時所留下的文物(如印度教、佛教雕像)可知,最遲在四至五世紀時,占婆就接觸佛教了。在七至八世紀的雕像上,可以看到受到泰國他叻瓦滴時期的造像影響,例如眼睛大,嘴唇厚,雙眉彎曲略微凸起,並在鼻根處相連等。另,觀音菩薩立像穿著短短的干縵,在肚臍附近打著衣結或皺褶。這可能與室利佛逝或高棉等地的雕像有關。
雖然占婆雕像以印度教為主,佛教居次,但佛像頗具特色。在八至九世紀的雕像上,不時可發現長長的編髮,其整體形狀略似頭盔;耳朵上有圓盤狀的大型耳環,背後則有長長的衣尾等。這些特徵甚少見於東南亞其他國家。九至十世紀時,東陽的雕像通常濃眉大眼;寬大的鼻子下,有厚厚的雙唇,嘴唇上留著大鬍子;兩鬢下有修剪得頗為整齊的短絡腮鬍。耳朵像前期一樣,大多很長,並且在耳垂上戴著圓碟狀的飾物;飾物表面有放射狀的線條或皺褶。十世紀時,美山(My Son)的雕刻頗為細緻。有些位在大型雕像底座的女性舞者(或樂師)的雕像,是公認的傳世傑作。
占婆的佛教雕像不僅特殊,還曾向外輸出,如泰南、中國雲南。占婆某些九到十世紀的觀音立像,全身細瘦,髮髻高高梳起;眼睛平視前方,臉豐唇厚,及肩的耳垂掛著精緻耳璫;上半身袒露,腹部肌理清楚,頸項、臂上、手腕都裝飾著瓔珞;腰際繫帶並打結,下半身的薄裙幾乎長達腳踝,裙上有細密的刻線,裙後可見腿部結構(但並非如笈多造像那樣衣薄貼體),這些特徵,可在大理的某些觀音像上找到,追本溯源,也不難在室利佛逝甚或南印度見到,表示東南亞區域內外有文化上的交流。
(六)印尼、馬來西亞
印尼、馬來西亞的銅像清楚地顯露受到印度的影響。千百年前,印度商旅乘風破浪開向東南亞,不久便開抵印尼(蘇門答臘、爪哇)、馬來西亞(馬來半島),反之亦然,這裡的商旅也可朝西北御風而行。自七、八世紀起,蘇門答臘、爪哇、馬來半島、泰南屬室利佛逝國,版圖之內,各地的藝術文化交流頻繁,由於往來頻繁,而且印度是多種宗教及其藝術(如雕像)的母國,小型雕像也容易攜帶,因此很多印度雕像出現在印尼和馬來西亞;王公貴族、護法信徒見了雕像心生歡喜,紛紛仿製。於是,印尼和馬來西亞與印度的雕像之間就有不少相似之處。
五世紀前印尼、馬來西亞的佛像不多,因當時這兩國並不流行佛教。據法顯(五世紀由印度經東南亞返國)記載:「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當時這兩國的雕像可能多是婆羅門/印度教的。近代馬來半島北部(吉打州,Kedah)出土一些佛像。主要的佛銅像呈三屈立姿;肉髻淺,臉頰豐,僧衣貼體猶如透明。左手在胸前執僧衣一角,但僧衣左側較厚並在小腿前稍微斜向右下,透露笈多或阿瑪拉瓦提的影響,其年代大約五世紀,出土的除了佛教文物之外,還有不少印度教的,印證了法顯之言。(但十四世紀前後,這裡慢慢伊斯蘭化,致使馬來半島的佛教雕像隱沒數百年)
接著,印尼佛像漸多。據義淨(七世紀下半葉經東南亞往返印度)言:「斯乃咸遵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遊少有大乘耳。」當時信南傳佛教的印尼人,遠多於信大乘。那時流傳至今的佛像不多,其中多屬南傳佛教的。八世紀時,印度佛教已富含密教色彩,影響及印尼。密教僧侶,如金剛智、不空等,相繼到唐朝譯經弘法,他們大多經由海路,很可能到過印尼或馬來西亞。
約自九世紀起,印尼佛教藝術的在地特色轉濃。當時,印度的佛教逐漸衰微,無法再提供源源不斷的活水;印尼的工匠藝人則把先前所吸收的種種風格予以綜合,加上在地元素,冶於一爐,創作新雕像。
日惹(Yogyakarta)的婆羅浮屠就頗具在地特色。整個婆羅浮屠蓋在直徑約108公尺的山丘上,遠遠看去,如一座階梯狀的金字塔,也像巨大的立體曼荼羅,所表現的應是大乘(如華嚴)及密教思想。其平面有基座、浮雕,浮雕刻劃地獄的種種慘狀,表達「善惡到頭終有報」的觀念。基座上是五層方形迴廊,它們一層層往上縮小。各層迴廊的石壁滿布浮雕,所呈現的是本生故事、《大方廣佛華嚴經》等。這些浮雕刻在緊密相連、層層相疊的方形石塊上;石與石之間的細縫儘量避開人物的臉孔,以免細縫穿過顏面。浮雕之間,每隔幾公尺就有一龕,每龕各置一圓雕佛坐像,總數逾四百。再往上,是三層同心、依序往上縮小的圓壇。每層各有鏤空的石塔,塔內各有一等身大小的佛坐像;三層共計七十二座。塔身及石壁都無浮雕。佛像素樸雅潔,僧衣緊密貼體,薄如蟬翼;眼睛半開,視線朝下。佛像所透露出來的平和、穩定、靜謐、安詳,以及內在所煥發的智慧之光,遠非言詞所能形容。這三圈石塔、其下數層迴廊、基座,如眾星拱月般環繞著頂上大塔。從下到上的層次,可解釋為佛教思想裡的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雖然婆羅浮屠的雕像可見受到印度的影響,但在地元素歷歷分明。例如,浮雕上多數人物的服飾、配件,背景中的建築、陳設、樂器、交通工具、動植物等,可能取材自當地的生活環境。在手印方面,爪哇匠人將不同手印用在不同位置的佛菩薩像上,並沒有完全依照傳統印度佛教藝術的規則。整個來說,婆羅浮屠是印尼佛教藝術的上乘之作。
與婆羅浮屠大約同時出現的小銅像很多。這些雕像大多站立,或坐在蓮花或須彌座上,其他的姿勢較少。坐像除了結跏趺坐(單盤或雙盤)之外,還有垂足倚坐像,垂下的雙足由蓮花或底座托著,這種姿勢較少見於東南亞其他國家。不少佛像臉形飽滿,有的如球莖;螺髮大,眼睛半開,嘴巴稍小;偏袒右肩,身上素雅,但可能有寶座、頭光、背屏或傘蓋,寶座常有飾物。頭光略呈長橢圓形,而且常在頭光或背屏的周圍滿布稍微拉長的火焰,用以象徵佛陀身心明亮、智慧清朗。傘蓋常與雕像連成一體,並有裝飾,這種作法也少見於東南亞其他國家。菩薩像大多頂戴高冠或高梳髮髻,胸口、臂膀、腰際多有精美的瓔珞珠玉;聖帶(聖紐、聖線)以「S」形自左肩斜向右腹;有的四臂,有的六臂甚至八臂,手結說法、無畏或轉法輪印。雕像的尺寸常在20~30公分內,可謂袖珍,且易於移動。
爪哇最佳的作品之一,出現於新柯沙里王朝(Singosari,1222~1292)。但這些佳作目前大多在印尼的殖民母國荷蘭,其中般若波羅蜜多菩薩像乃代表作之一。此般若波羅蜜多菩薩像頭戴華麗寶冠,結轉法輪印,左手臂上有一蓮花,全身滿布瓔珞;頭光和背屏向上拉長,呈橢圓形,頗為美觀。整個來說,雕工細膩,風格上融合各家,而非印度某時某地的,據傳此雕像以當時皇后的容顏為模型製作。十三世紀末起印尼逐步轉向伊斯蘭教,在雕像上也有了變化。浮雕的典型作法之一,是在空間關係的處理上漸漸從三度空間變為二度空間,本來見於婆羅浮屠上、盛大的皇家隨從陣仗,此時已然不見,有時甚至連應該盛裝的國王、皇后等像,也沒有相稱的服飾。
這時,印度文化於印尼「在地化」的情況普遍發生。爪哇詩人向內容豐富的印度史詩汲取靈感,譜出屬於印尼本身時空場景的曼妙生動新作,同樣地,雕刻家也自印度史詩擷取神話傳說,將裡頭的男女主角、英雄好漢、各種感人的情節等巧妙地剪裁,融入印尼的雕像中,例如主人翁所穿戴的服裝、頭飾是印尼的,而背景中有在地的熱帶植物。印尼漸漸涵攝了印度佛教雕像的傳統,並隨著時間推移,一步步注入自己的色彩。
整個看來,東南亞雕像確實受到外在文化的啟發,但本身的角色一樣不可忽視。實際上東南亞迸出了鮮活的創作力,並推出五光十色的雕像,這種情況,可譬喻如天降大雨時,大樹中樹小樹、各種花草樹木都從中吸收水分,得到滋潤(東南亞佛像也從外來文化中汲取養分);有趣的是,各種植物喜獲甘霖,但各自依照本性、長成不同的模樣,吐露各色花朵、結成多種的果實(東南亞也在吸收各種外來養分、彼此切磋琢磨後,不斷推出新的作品)。無論是佛像主題、形式、風格等,在時間的長流中,東南亞都有獨到之處,這些都增益了東南亞藝術的內容,也深化了佛教藝術的內涵。
|
相關詞條:藥叉女像, 佛立像, 菩薩立像, 獅子柱頭, 佛坐像, 彌勒菩薩像, 阿瑪拉瓦提佛塔圖, 龍樹丘遺址佛立像, 佛立像, 佛立像, 佛坐像, 菩薩坐像, 奧卡那大佛, 觀音菩薩像, 多羅菩薩像, 菩薩立像, 菩薩像, 釋迦牟尼佛龕像, 佛傳圖, 佛坐像, 佛坐像, 麻浩崖墓佛坐像, 菩薩立像, 釋迦牟尼佛坐像, 佛坐像, 菩薩立像, 麻浩崖墓佛坐像, 陶佛像搖錢樹座, 銅佛像搖錢樹, 釋迦牟尼佛坐像, 阿彌陀佛立像, 董欽造阿彌陀佛及脇侍像, 范氏造阿彌陀佛及脇侍像, 馬周造佛坐像, 龍門石窟第1280窟奉先寺盧舍那佛像, 十一面觀音菩薩龕像, 姚元景造一佛二菩薩龕像, 楊思勗等造一佛二菩薩龕像, 觀音菩薩像, 九面觀音菩薩像, 虛空藏菩薩像, 龍門石窟第2050窟擂鼓台南洞菩提瑞像, 華嚴寺下寺菩薩像, 獨樂寺脇侍菩薩像, 奉國寺七佛像, 善化寺大雄寶殿造像, 佛光寺文殊殿造像 , 延嘉七年銘佛立像, 軍守里佛坐像, 瑞山磨崖佛三尊像, 觀音菩薩像, 觀音菩薩像, 金銅佛三尊像, 法隆寺金堂壁畫, 阿彌陀佛立像, 佛坐像, 石窟庵普賢菩薩像, 法住寺磨崖佛倚坐像, 灌燭寺彌勒菩薩像, 觀音菩薩像, 飛鳥寺釋迦牟尼佛坐像 止利, 飛鳥大佛, 法隆寺釋迦三尊像 止利, 法隆寺釋迦三尊像 止利, 法隆寺觀音菩薩像, 法隆寺觀音菩薩像, 中宮寺菩薩半跏像, 思惟菩薩半跏像, 當麻寺彌勒佛坐像, 藥師寺藥師佛及脇侍像, 觀音寺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眾寶王菩薩像, 東大寺盧舍那佛坐像, 十大弟子像 將軍萬福, 八部眾像 將軍萬福, 太子降生像, 東大寺不空●(上四+下絹)索觀音菩薩像, 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東大寺四天王像, 新藥師寺十二神將像, 神護寺藥師佛立像, 廣隆寺阿彌陀佛坐像, 神護寺五大虛空藏菩薩像, 觀心寺如意輪觀音菩薩像 (傳)真紹, 神護寺藥師佛立像, 新藥師寺藥師佛坐像, 藥師佛立像, 法華寺十一面觀音菩薩像, 勝常寺藥師佛及脇侍像, 法性寺千手觀音菩薩像, 平等院阿彌陀佛坐像 定朝, 法界寺阿彌陀佛坐像, 淨●(王+留)璃寺阿彌陀佛坐像, 臼杵磨崖佛像, 大谷寺石窟, 阿難陀塔寺佛像, 觀音菩薩像, 婆羅浮屠, 阿尼哥, 巴方寺
|